白雪皚皚的幌舞車站,高倉健飾演的佐藤乙松和十幾年前一樣,等待著火車的進站,他為了工作而犧牲掉了作為丈夫和父親的首要責任,當鏡頭每一次給到高倉健的臉上,總會讓人覺得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憋悶之感。
這位鐵道員的一生都在為自己的崗位堅守,以致于忽視家人,也許這個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覆蓋在白雪之下的車站班次越來越少,乘客也寥寥無幾,連他最好的朋友仙次都不得不離開這里另謀生路。
他不是穿越太空的宇航員,不是浴血奮戰、保家衛國的戰士官兵,也不是乘風破浪的無畏艦長,他只是一個即將被廢棄的車站中的一個站長,他甚至只是個“光桿司令”。
日本電影《鐵道員》
我們可能很難理解,就是這樣一個看起來沒有多大價值的工作為何能令他犧牲家庭,面對在家庭中的失職,他顯得手足無措,于是他對著天空吹出一聲哨笛,正如他的老朋友仙次所形容的:
“以揮旗來代替憤怒,以笛聲代替眼淚,以內心呼喚來代替吶喊,這就是鐵道員。”
但從日本的民族性格上來說,他又相對符合我們對于日本人那極度的隱忍和克制,以及做事講求原則,卻又死板,缺少變通的固有印象。
劇中的佐藤乙松帶著某種偏執與執拗,在他眼中,公德大于私德,工作職責高于家庭責任,一句:
“這個崗位離不開我”
成為了他的座右銘。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種價值觀,在常人看來,工作的目的就是為了養家糊口,實現自我價值的同時,讓家人能夠體驗到更好的生活。
日本電影《鐵道員》
然而鐵道員佐藤乙松卻陷入了一種謬論當中,我們可以設想,當幌舞車站沒有出現佐藤乙松的身影,那么隨之可能引發最嚴重的后果便是火車出現事故,但在家庭事故與社會事故中,他選擇了大公無私,這是唯一能讓他感到欣慰,并能讓他用作自我原諒來麻痹自己的方式。
在十二年前,佐藤和妻子醞釀出一女,但剛出生沒多久的女兒就患了重感冒,因佐藤要堅守崗位從而沒有陪同妻子一起送女兒去醫院。最終,姍姍來遲的佐藤看見的是自己女兒冰冷的尸體,這是多么的殘忍的一幕,無論對于鐵道員佐藤乙松,還是銀幕前的觀眾,導演用最無情的方式把這個問題拋到觀眾們面前。
日本電影《鐵道員》
幌舞支線的列車上只有妻子和亡女,佐藤乙松走上車廂,妻子對他說:
“女兒已經死了,你竟然還能揮著旗子迎接她”。
佐藤乙松說:
“有什么辦法,我是鐵道員”。
女兒夭折后不久,由于他沒有長時間陪在妻子身邊,導致妻子一直在女兒去世的陰影籠罩之下,最終也郁郁而終。他的悔恨伴隨著他之后的一生,對亡妻,對夭折的女兒,他充滿自責,但對于工作的忠誠代表著某種正義,這多少能使他內心當中的負罪感得到一些消解。
日本電影《鐵道員》
影片的最后,佐藤乙松見到了夭折的女兒,導演利用了一種象征性手法讓成為亡魂的女兒雪子在幌舞車站與父親佐藤乙松見面,在暖和的站長休息室內,外面大雪紛飛,雪子為父親做了一鍋湯食,兩人捧著熱乎乎的飯菜,畫面極其的溫馨。
除了廣末涼子飾演的“第三階段”的雪子,前面兩次不同年齡段的雪子也曾因某些偶然因素和佐藤乙松見過面,但當時佐藤已松并未能夠認出這是自己的女兒。
看到如此溫馨的一幕,觀眾們和佐藤一樣,心底的灰燼再次重燃,原來雪子沒有死,這大概是所有觀眾們的集體訴求,人們想給佐藤一次機會,也給這個破碎的家庭一個希望。
日本電影《鐵道員》
但最終當佐藤從醉酒中醒來,雪子早已消失的無影無蹤,雖然至今觀眾們仍然愿意相信辦公桌上的人偶,和飯桌上還冒著熱氣的熱湯是雪子到過這里所留下的線索,但筆者認為,這只是觀眾們的一廂情愿,那天夜里,在雪子離開之后,人們在第二天早上發現了佐藤乙松浮在雪堆上的尸體。
女兒雪子在那天晚上曾說過,之所以前幾次見面沒有表明自己的身份,是因為怕自己是鬼魂而嚇到父親,而父親那句話不知道感動了銀幕前多少觀眾:
“怎么會害怕呢,世上哪有父母會害怕自己的子女”
。
日本電影《鐵道員》
在佐藤乙松生命中最后的那幾個小時的時間里,他和女兒達成了和解,亦或者說,他在想象中讓女兒理解并原諒了自己的所作所為。在他的臆想中,他向女兒雪子道了歉,他承認自己沒有盡到父親和丈夫的責任,得到了女兒一句:
“雪子一點也不介意!”
的安慰后,他便從心靈上如愿以償的得到了救贖,我們都知道,在現實當中,佐藤乙松根本沒有機會去向女兒和妻子表達這些愧疚,也許也不可能得到她們的原諒。
從前,他在離開人世之前有些忐忑,他怕妻女不會原諒他,不會理解他,不會接受它,而當天晚上雪子的出現為他自己去另一個世界跟妻女團聚掃平了障礙,最后他不帶有任何遺憾,安詳地離開了他熱愛的工作崗位,離開了這個世界。
日本電影《鐵道員》
這部拍攝于1999年的日本影片并未給觀眾編制一個特別大的格局,只是向我們展示著一個普通鐵道員在工作和家庭中的矛盾體現,說到底不過是事業和家庭,孰輕孰重,如何去平衡的問題。題材看似并不新穎,但對于這個世界性難題,導演
降旗康男
本身其實并沒有給出自己明確的答案,他只是把這種沖突與矛盾以一種極端的方式上升到生死的層面,用以增加它的深刻程度,并毫無擔當的把這個問題拋給觀眾。
這是一部典型的日本影片,區別于
是枝裕和、河瀨直美
等另外一類治愈系電影,在此類型的影片當中,導演并不負責呈現正確答案,也不借助任何外力形式上的和解,而只是將一種極端的后果展示給觀眾,并用角色本人自我麻痹的方式去與自己的內心進行和解。
日本電影《鐵道員》
在筆者眼中,這部電影可能是高倉健最好的電影,一個優的演員的卓越技術不體現在“放”,而體現在“收”,就如駕校老師說的:“只懂得踩油門的司機永遠只是愣頭青,學會了如何控制剎車的司機才是老手”。毫無疑問,高倉健在電影《鐵道員》當中,貢獻出了自己非凡的演技,他將片中角色佐藤乙松在悲劇面前所持有的隱忍刻畫的細致入微,他通過面部的細微變化來控制情緒,讓當事人的情感表現極其逼真。
那一年,68歲的高倉健,24歲的安藤正信,19歲的廣末涼子在邁進21世紀的門檻前為我們帶來了一部足以銘記一生的經典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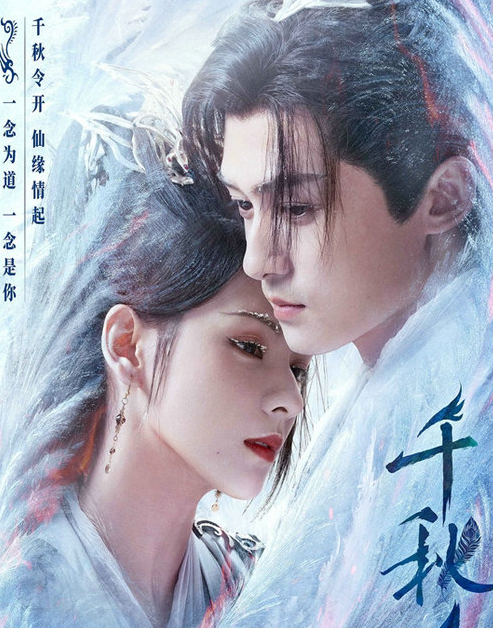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