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國早報記者 覃江宜
從1993年的《超級馬里奧兄弟》,到2022年正在熱映的《神秘海域》,三十年間越來越多的游戲人物邁向大銀幕。作為這個時代的“第九藝術”,電子游戲逐漸像上世紀末的漫畫一樣,成為了電影取之不竭的靈感來源。
然而,這個跨界歷程向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因為游戲迷幾乎是最難討好的一個群體——在他們熟悉的虛擬世界,自己才是那個上天入地無所不能的主角。而在觀看電影的過程中,他們只是一個被動的旁觀者。熟悉的觀感一旦被破壞,落差隨之產生,于是“愛的越真,怨念越深”。
其實,電影和游戲都是“造夢”的藝術,幫助受眾短暫抽離于當下的庸常生活。不管誰借鑒了誰,誰改編了誰,真正重要的是:能否用一種別出心裁的方式,帶來一段色彩斑斕的冒險,給人們帶來靈魂出竅的感動。
A 上映的游戲那么多,成功的沒有幾個
游戲改編電影“十個改編九個爛”?是的,從1993年熱門游戲《超級瑪麗》被改編成《超級馬里奧兄弟》開始,游戲就成為了電影世界里最被期待也最被嫌棄的主題。
把游戲主角請上大屏幕,創意一開始還能讓觀眾耳目一新。1993年香港電影《超級學校霸王》請來了劉德華、張學友、郭富城、鄭伊健等明星壓陣,時至今日在豆瓣仍有7.5的高分;1994年環球影業發行的《街頭霸王》成本3500萬美元,全球票房9942萬美元;1995年獅門影業發行的《真人快打》成本2000萬美元,全球票房1.2億美元。游戲人物變身電影主角,用各自的絕招,解現實的困局。憑借游戲迷的“情懷殺”,飲“頭啖湯”的片商們賺得盆滿缽滿。
口碑是什么時候急轉直下的?一個成功案例的背后,是無數跟風的平庸之作,《格斗之王》《生死格斗》《鐵拳》《毀滅戰士》……當街機廳走出來的“格斗家”扎堆亮相大屏幕,觀眾很快審美疲勞了,因為他們發現熟悉的主角除了不停歇打斗,就是無休止惡搞,一個個口號大義凜然,情節卻如同低幼的兒戲——想象一下,若《三國演義》“赤壁大戰”的名場面剔除“舌戰群儒”“蔣干盜書”等一干文戲,變成“周瑜無腦單挑曹操”的無聊戲碼——如此,電影便淪為了一場糟糕的cosplay(角色扮演),普通觀眾看得云里霧里,鐵桿玩家則恨不得要手撕導演。
繼“格斗家”之后,一個個“探險家”“賽車手”“特工”乃至“萌寵”,接連登陸影視圈,多數逃不脫“撲街”的命運,導演們也就越來越不愿意打一場真刀真槍的攻堅戰。
2016年上映的《魔獸》是一座高山,作為目前游戲改編電影的全球票房冠軍,它與《魔戒》影視化的成功有異曲同工之妙:《魔獸爭霸》本就是游戲界的頂流,“艾澤拉斯”照亮了觀眾的青春回憶,電影用大片質感還原了原著中恢宏的世界觀架構,有可信的人物,扎實的故事,許多人也就愿意為情懷買單。
了解這些背景,就知道為什么剛剛上映的電影版《神秘海域》從項目籌備到正式上映相隔了10年,其間6次更換導演,生生把湯姆·赫蘭德從少年配角熬成了成年主演。有太多“翻車”的先例,觀眾不再那么容易被糊弄,這買賣不再像當年那么“一本萬利”。
B 討好游戲迷,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片商們對熱門游戲的偏愛不難理解,大IP知名度在前,電影可以做到未映先火,廣泛吸引玩家和路人觀影,這是票房的保證。但這同樣是口碑的陷阱,因為游戲迷幾乎是最難討好的一類觀眾,尤其是愛得深沉的鐵桿玩家,往往容不得半點偏題和戲說。
游戲迷曾經是知足常樂的,早期的電子游戲畫面簡單,主角只會打打殺殺,背景故事多是字幕一筆帶過,仿佛一張白紙可以任意涂鴉。電影寥寥幾筆勾勒,就能為原有的故事錦上添花,讓虛擬人物弧光飽滿。所以,香港導演王晶用了不到半個月就拍出了《超級學校霸王》,只是故事情節粗制濫造,充斥著大量戲謔橋段。例如,僅僅因為“四大天王”中的黎明拒絕出演,王晶就強行塞入了一個叫“黎明”的丑角,把“黎天王”黑得體無完膚。
這部香港無厘頭電影的代表之作,在《街頭霸王》的框架里一口氣塞進了《終結者》《機器貓》《七龍珠》《超級瑪麗》等近10個熱門游戲……一鍋亂燉的大雜燴卻看得當時的游戲迷心花怒放。在豆瓣前置的評論里,有網友感慨說:“當年光是看到這些明星,感覺就值回票價了。”
類似的作品如果在今天上映,毫無疑問會被歸于爛片的行列。明星(或者說知名游戲)的曝光無孔不入,粉絲們不再需要用電影來親近偶像。而電子游戲的世界觀越來越宏大,游戲迷們已經擁有一個天馬行空的世界了,怎么會滿足于簡單的戲仿與致敬?電影拍得過于忠實原著會被嫌棄“毫無新意”,改動過大則被視為“胡編亂造”。
近年來的游戲改編電影還是有過幾對“天作之合”的:安吉麗娜·朱莉的“勞拉”(《古墓麗影》),杰克·吉倫哈爾的“波斯王子”(《時之沙》),米拉·喬沃維奇的愛麗斯(《生化危機》)。他們贏得觀眾的秘訣,首先在于契合游戲的外型與氣質,看這群自帶流量、演技過硬的大明星再現各種經典場面,同時又開辟了新的故事線。有情懷濾鏡的玩家,沒思想包袱的觀眾,才能在電影院里皆大歡喜。
C 電影已經“老”了,而游戲正年輕
從粗糙的像素方塊,到鮮活的虛擬世界,不斷進化的電子游戲,已經在多個維度悄悄完成了對于電影的追趕(乃至超越)。從某種程度上看,游戲能夠提供比電影更深入的沉浸感,主角所感受到的一切,包括內心深處的每一個想法,所有的情緒起伏,都會直接傳遞給屏幕前的玩家,以層層暈染的方式,形成一場情感共振。
近年來的《最后生還者》《行尸走肉》《這是我的戰爭》《巫師3》等游戲大作,都在講述一種令人動容的故事,并提供直擊人心的互動體驗——
《這是我的戰爭》里,在末日里為了獲得生存資源的主角們,往往要面臨殘酷的兩難抉擇:如果為了救助親人,必須傷害他人的利益呢?如果要抵達目標,必須踐踏同伴的身體呢?這是日常生活中極少會遇到的人性拷問。
《成為人類》展示的未來社會,三個仿生人分別懷揣著“保護愛人”“族群權利”和“自我認同”的目標上路,在命運的糾葛中身不由己,每一次為他們作出選擇,就指向不同的方向和結局。在這里,玩家同時擔當了“導演”和“主角”。
前后歷經七年的電子游戲《行尸走肉》中,開場時“克萊蒙婷”只是個隨波逐流的懵懂少女,在劇變過后的世界中艱難求生,可極端情境就像巨浪一樣不斷來襲:最后一塊面包,是要留給自己,還是留給奄奄一息的路人?兩個一路相隨的同伴必須舍棄一個,應該犧牲誰?在一起經歷了各種考驗后,你無法再將NPC看成一個虛擬人物,不是可以輕易舍棄的“沉沒成本”,“他們”就像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沉浸這些游戲的時候,全世界無數玩家都有過柔腸百轉、長吁短嘆的糾結時刻,仿佛在經歷真正的人生關口。這種強調“陪伴”和“養成”的參與感,使得行至百年的電影概念顯得老氣橫秋。而承載更多互動技術的電子游戲,可能才剛剛進入青年時代。
D 真正講好一個故事,比什么都重要
在“元宇宙”呼嘯而來的當下,電影和游戲始終在技術與敘事上不斷相互學習,電影改編游戲,游戲也在學習電影,比如,《古墓麗影》系列從游戲變成電影,《瘋狂的麥克斯》卻從大銀幕走進顯示器。許多年前,電影《羅拉快跑》就在敘事結構上借鑒了游戲的“讀檔”功能。后來,很多游戲也借鑒著電影鏡頭營造“大片感”(如《黑客帝國》的“子彈時間”),設計出令玩家贊嘆的酷炫場面。
從民間傳說到書籍、再到漫畫和游戲,電影作為一個兼容并蓄的文化載體,必須要對日新月異的電子游戲另眼相待。
蹭蹭熱度就能火?不可能。你看,電影《寂靜嶺》之所以能拿下IMDB最高評分(游戲改編電影類),在于導演克里斯多夫·甘斯、編劇羅杰·艾福瑞都是《寂靜嶺》的忠實玩家。與那種只想收割熱度的主創團隊不同,他們太懂這個游戲何以動人,故事里宗教隱喻與人文內涵要如何解構。因此,粉絲們看到了“神還原”的場景與人物,打開了新的想象空間,而不僅僅是重溫了一遍耳熟能詳的故事;觀眾進入了一個二元交替的異度空間,電影版《寂靜嶺》完成了創意“出圈”,那股積聚不散的濃霧里,繼續回蕩著道德拷問的鼓聲。
不同的時期,故事有不同的講述方式,它們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而是交融與共生。正如大衛·芬奇所說,“說到底,真正重要的是具備想象力的好故事,無論其以什么形式呈現”。所以,電影和游戲還將攜手上路,而對于我們來說,值得關心的問題只有一個:怎樣才能把一個好故事說得蕩氣回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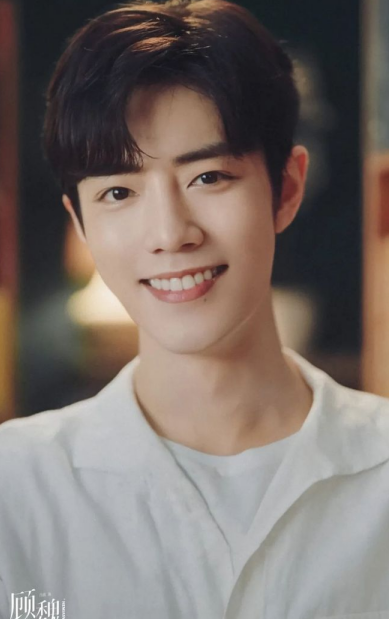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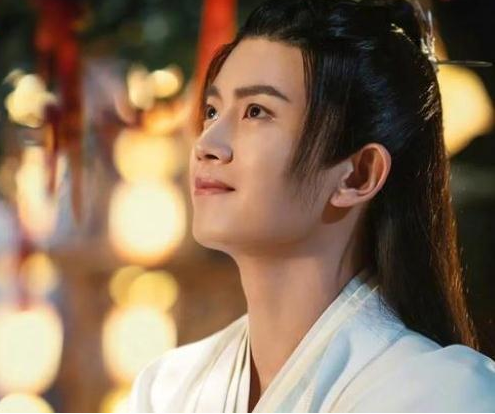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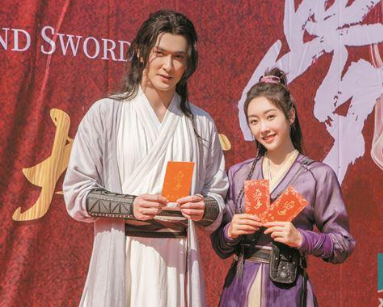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