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申明:本文為@影吹斯汀 獨家原創稿,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抄襲or轉載,違者必究!】
今日繼續影展系佳片推薦~這一次給大家帶來的,是最近釋出資源,由韓裔導演郭共達執導,科林·法瑞爾主演的科幻電影《楊之后》。
盡管陣容不算知名,但影片還是以不太受藝術電影界待見的科幻片身份,入圍了去年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首映后更被稱贊有“令人震撼的深度”以及“觸及人性核心的感動”,整體口碑不俗。
影片改編自亞歷山大·韋恩斯坦的短篇小說《向楊說再見》,講述未來世界里,人類與機器人之間的相處故事。
但完全不同于強調宏大世界觀、激烈人機矛盾與炫目特效場面的科幻大片,整體氣質“小而美”的它,另辟蹊徑,以跨文化的視角,把各類東方元素有體系地融合到這個“西方感”十足的類型片種里,頗具新鮮感。
影片的雋永風格與文化新鮮感,首先表現在故事設定上。
《楊之后》放棄了科幻片開頭由大到小的背景信息介紹,直接從一個多族裔家庭的日常生活切入。科林·法瑞爾飾演的男主角是一位茶店老板,他與黑人妻子領養了一個可愛的華裔小女孩美香。
為了讓女兒更好地了解故鄉文化,他們特意選擇了一位深諳東方文化、外形上也是標準黃種人的二手機器人“楊”,作為“哥哥”,一直照顧、教導她。
四人的日子也過得非常和諧,但在一次家庭舞蹈比賽結束后,“楊”出現了故障。為了“拯救”這位非人類的家庭成員,父親輾轉于各類維修機構,求助各色人物,最終找到了一塊獨屬于“楊”的記憶存儲器,發現它竟然也有深藏心底的秘密。一家人對機器人的態度隨之徹底改變……
科幻大類之下,《楊之后》講的其實是一個“尋找-發現”的故事。
為了確認“楊”具體的故障,父親反而揭開了另一層真相——這個機器人竟自主保留了獨屬于它的“記憶”。盡管記憶是人類的基礎能力,但對于這樣一類服務型機器人來說,依然是不可思議且難以解釋的高級智慧。
父親正在進行時的尋覓行為,也變成了一次記憶的回訪,串聯起大家對“楊”的回憶,以及它自身的秘密。
通過讀取“楊”封存的文檔,父親發現,原來早在購買它之前,“楊”就已在另一個單親家庭工作多年。
“楊”曾目睹前雇主家的兒子在成人后離開家庭,留老母親終老。即便有它的照顧,老母親也無法擺脫孤獨和悲傷。作為一個外來服務者,它始終沒能真正融入家庭。
但理療師Ada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在與她的相處過程中,“楊”感到快樂、松弛,甚至體會到類似愛情的感受。
照顧Ada侄女的經歷,也讓它體驗到前所未有的親情和友誼。他們的相繼離開,更讓這個本該“沒有感情的服務機器”,見識到“死亡”和“分離”的痛苦。
盡管來到新家后,它被重啟了裝置,但這些關乎情感和生命體驗的記憶,還是被保留了下來。“楊”的記憶、思維、感受能力,也在這個視它為親人的新家庭里,得到進一步發展。
美香對它如哥哥般的依賴,家人對它的信任,以及日常生活里的植物嫁接術,茶葉的品味之道,亦或是系統知識庫里的老莊哲學,都成為它主動保留的記憶片段,更觸發了它對“存在”和“生命”的思考。
“楊”最后的“故障”,也不是偶然,更像它計劃已久的自我終結。
機器人思慮多時的“主動離開”,對這一家三口而言,更像一次悲傷的意外——親人的死亡。盡管“楊”并非人類,更談不上什么親緣關系。
但美香的不舍,這對夫妻一直試圖壓抑的慌亂、焦慮、痛苦,都反向證明了這個機器人“生活過”的痕跡,和無法取代的價值。“有無相生”的老莊哲學,通過它的離開得到彰顯。人與機器之間的界限,也在情感、記憶、時光的交錯共振中,被悄然取消。
這也體現了《楊之后》的巧思,即在東西方文化、家庭與科幻類型的交界處,找到了一個大多數人都能接受的融合點。
其實,從家庭人員的族裔設定來看,影片并沒有過分強調“東方”的概念,而是傾向于暢想一種未來世界的境況——國家、種族、文化的藩籬已不復存在,作為社會原子結構的家庭,已經成為了多元共存的和諧容器。
片中,白人男性會迷上茶葉文化,在家宅里設立品茶室。黑皮膚的女人則成了家庭的經濟棟梁。亞裔養女更是所有人疼愛的對象。在科技的助益下,傳統的性別框架、種族文化偏見都被最大程度紓解,世界迎來了更美妙的包容與和平。
通過一個小小的多元家庭,《楊之后》便確立了一部科幻片,對“技術”和“未來”的總體樂觀態度,而這也與我們當下愈加分裂、動蕩的生活,形成別有意味的映照。
隨著故事的發展(記憶的探索),老莊的哲學思想(有無相生)、茶葉的品味之道(風味背后是對時空、地理、文化的想象性體驗)等劇情上的東方元素,也成為影片探討“記憶”、“人機關系”、“存在”等哲學議題的觸發點。
而這,也與西方科幻片里的人類終極話題思辨(如:何為人的“存在”、人與宇宙萬物的關系等,參考《銀翼殺手》),產生了跨文化的共鳴。
即便討論出的結果不算深刻,導演對于中國道家文化的理解也比較表面,但這種借用文化資源表達共通議題的聰明巧勁兒,在我們自己的電影創作中反而鮮見。
作為一部主打科幻哲思,成本不高的“軟科幻”電影,外觀簡樸不鋪張的《楊之后》,也沒有在“科幻感”上露怯。
影片沒有一板一眼地秀裝備以凸顯超現實的技術想象,而是在日常里,以自然的生活細節和場景,呈現科技的應用水平。
自動駕駛的轎車,日常相伴的siri,便捷的語音指令,戴上即可觀影的墨鏡…來自生活,也高于我們目前的生活,看上去有未來感,但也不會破壞家庭故事的平實風格。
視頻對話時使用特殊畫幅和熒光濾鏡
為了呈現“記憶”和“死亡”的主題,暗示“楊”的故障狀態,影片特意在流暢的回憶畫面里,增加了碎片化的臺詞重復,以此制造機械短路、記憶失調的不悅“聽感”。看似單調(乃至突兀)的聲音復刻,也在物是人非中,激發微妙的感懷情緒。
在視聽和空間設計上,影片的“東方”屬性或許更加明顯。
相對穩定的機位,沉穩舒緩的構圖,不飽和曝光的畫面鏡頭,以及悠長又不失哀愁情緒的鋼琴、大提琴配樂,都切合著這個主打“回憶”的細膩故事。演員沉靜內斂的表演,中西風格共融的室內設計,也為影片增加了質感。
在中國科幻片在工業美學的道路上奮力追趕好萊塢之時,整合東方文化資源、從“小”入手,向古尋根的《楊之后》,也算為我們的科幻事業,提供了“宏大”、“硬核”之外的另一種思路吧。
(文/mo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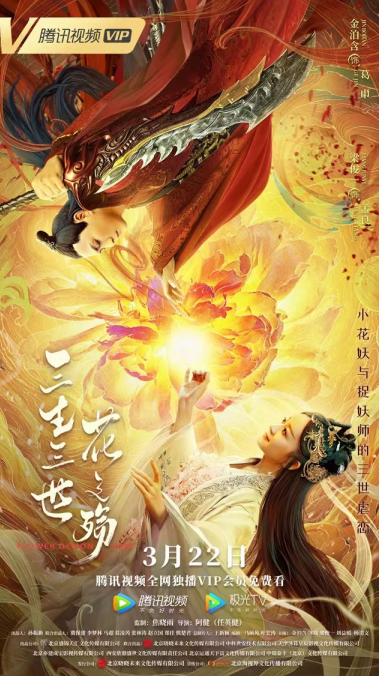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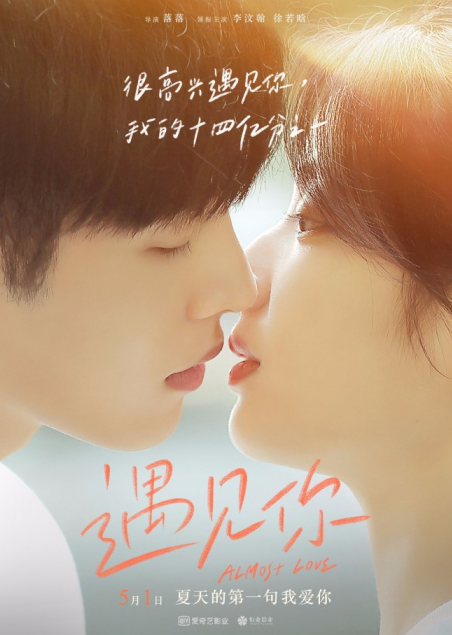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