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拳姐,一個專業吃瓜的深度影迷。第94屆奧斯卡頒獎典禮如期舉行,算是影視圈難得的一大盛事。
奧斯卡存在的意義和價值無需多言,它幾乎聚焦了所有專業人員和影迷們的目光,尤其是最佳影片和最佳男女主角三個獎項。當然,也有各種抓馬的紅毯名場面。
接下來,拳姐就帶大家一起淺析本屆和以往6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我們一起在電影中感知生活、頓悟人生。
2022年 《健聽女孩》,無聲和有聲兩個世界的對抗與理解。
《健聽女孩》(本屆最佳改編劇本獎)導演是夏安·海德,該片翻拍自法國電影《貝利葉一家》,講述了一個在聾啞人家庭中成長起來的女孩露比。她一出生就拿到了最困難的劇本,要為父母和哥哥充當“傳譯員”,與原生家庭充滿羈絆。
好在,最后露比經過一番掙扎與成長,最終考上伯克利音樂學院,并最終與家人和解。值得一提的是,《健聽女孩》英文片名為《CODA》,意為Children of Deaf Adults,聾啞人撫養下的健聽一代,這無疑是一種極具人文關懷的敘事視角。
與《健聽女孩》類似的講述少年與家庭矛盾的影片比比皆是,但《健聽女孩》最大的不同,是將雙方之間的矛盾,從以往的打架、墜落、爭執,轉換為有聲與無聲世界的激烈對撞。這種被聚焦、放大的青春期微妙心理,對觀眾有最直接的沖擊力。
值得一提的是,《健聽女孩》是使蘋果成為首個拿下奧斯卡最佳影片的流媒體平臺,也算是改寫了奧斯卡的歷史。
2021年《無依之地》,一首關于喪失的旅途詩歌。
《無依之地》由中國導演趙婷執導,奪下奧斯卡最佳影片后繼母宋丹丹也發文稱贊趙婷“你是我們家的傳奇。”
拋開這點娛樂邊角料來看,美國其實有許多公路電影,或者說講述人口老年化的作品,但為什么趙婷的《無無依之地》毫無懸念奪下冠軍?——因為一份情感上的克制,以及創造了一種新的電影類型,即類記錄虛構電影。
《無依之地》故事很簡單,講述了女主弗恩(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 飾)在經濟大蕭條中失去了工作和家園,后來住在房車中一邊打工一邊旅游,并遇到了各色各樣的人的故事。
片中大部分取材都是真實人物、場景和社會背景,絕大部分的演員都是素人。趙婷會根據素人的真實故事為其定制角色和對白,使得作品更加貼近現實,讓觀眾深刻洞悉了美國某個社會的真實面目。
此外,趙婷雖為導演,但她更像一個局外人,她的鏡頭始終與觀眾保持克制。
即無意批判怒斥,也不曾刻意抒情,而是夾雜著平靜的悲憫、頑強的樂觀復雜情緒。它社會層面、情感層面都有涉及,但都不會過分強調,因此它的可解讀性就會更寬闊。
2020年《寄生蟲》,用決絕的超現實方式刻畫社會赤裸真相。
《寄生蟲》出自韓國殿堂級級導演奉俊昊之手,是韓國影史第一部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奉俊昊憑借《殺人回憶》奠定了自己影壇地位之后,還曾拍出《漢江怪物》《雪國列車》等多部風格迥異的絕佳好片,擅長將社會議題用藝術化的方式表達。
電影《寄生蟲》中主角是貧窮的一家四口,貧窮家庭的大兒子通過一張偽造的文憑,一步步帶領爸爸媽媽和妹妹一起入侵富豪家庭。【寄生】在富豪家庭的過程中,貧富差距極大的兩家人因一連串的意外事件最終都遭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電影本身的制作,無論是從剪輯,節奏,符號上都精致完美的到無可挑剔,通過簡單直白的方式來制造落差,用戲劇化情節設計來誘發故事沖突。
猜不到的劇情反轉,精妙的處理節奏,諷刺的人物對立,在集荒誕驚悚懸疑與一體氛圍中,觀眾被導演牢牢牽引到了故事里。
《寄生蟲》無疑是一個令人悲哀的故事,但在現實生活中,如此兩極分化的差距卻隨處不在上演。電影通過一個故事把社會問題具象化,讓大家能夠更加關注到這些無法融入到社會中的邊緣人的同時,也給大家提供了一個思考社會現狀的空間。
2019年《綠皮書》,用低級無聊的笑話講好了一個正經故事。
《綠皮書》是一部真人事跡改編的劇情片,由維果·莫特森、馬赫沙拉·阿里主演。該片講述了白人保鏢托尼被黑人鋼琴家唐所雇用,兩人一起從紐約開始舉辦巡回演奏會,一場跨越種族和階級的友誼就此展開的故事。
彼得·法雷利執導的電影一直以充斥低級和無聊的笑話出名,作為一部標準的公路電影,《綠皮書》中也充斥著不少令人捧腹的笑料。比如優雅精致的紳士唐不愿吃黑人速食【炸雞】,但在托尼的百般誘惑之下,唐還是選擇了向美味妥協,翹起蘭花指捻起了他的第一塊炸雞......就此唐也開始放下自己所有的偏見,撕掉了種族的標簽。
作為一部捧回三座小金人的奧斯卡大滿貫作品,《綠皮書》想要表達的并不僅僅只是種族上的區分,而是通過講述一個粗暴的白人混混司機和一個儒雅的黑人鋼琴家的故事,來教會大家如何反擊不公平,如何捍衛自己尊嚴和權利。
不公平永遠都會存在,唯有鼓起勇氣正面對抗,才能最終戰勝惡意。
《綠皮書》是一部非常規整的電影,隨著劇情一步一步地推進,大家的情緒也隨之被調動,該笑的時候能笑,該哭的時候能哭,整個觀影的節奏被導演把控的精準到位。
作為一部成功影視作品,故事的精彩固然重要,但能夠營造一個讓人沉浸其中的舒服氛圍,才是真正的難得。
2018年《水形物語》,不僅僅是只有愛情的成人童話。
《水形物語》出自名導吉爾莫·德爾·托羅之手,吉爾莫作為享譽世界的“怪獸迷”,還曾拍出《地獄男爵》《潘神的迷宮》《環太平洋》等經典作品,吉爾莫所打造出的光影世界中似乎永遠都充斥著一種怪誕的魅力。
作為2018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的贏家,《水形物語》的整個故事并不復雜。冷戰時期的聾啞清潔工伊莉莎在實驗室中發現了被折磨得“人魚怪獸”,兩個孤獨的靈魂在冰冷實驗中秘密交往,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愫也在兩個生命體中悄然產生,于是伊莉莎決定幫助“人魚”回到大海。
追求愛與自由的故事比比皆是,但《水形物語》能夠拿下大獎最重要的原因,其實是故事中的【人文關懷】。電影通過想象或者和神話的美麗來進行對比,把殘酷的現實和傳奇神話當中不可能實現的東西結合在一起
——通過邊緣人物的視角來刻畫一個理想的現實世界,憧憬人性的美好的溫暖。
在這部電影中,我們看到了美與丑,光明與黑暗,傷害與救贖,壓迫與反抗......在如此強烈的兩級沖突之下,讓人不禁思考,我們究竟是人形的怪獸,還是怪獸形狀的人。
2017年《月光男孩》,關于成長的詩意寓言。
《月光男孩》的導演是巴里·杰金斯,該片講述了喀戎從孩童到青年時期,逐步發現自己的性取向,經受外界非議和內心掙扎后,找到真正自我的故事。
喀戎年少因瘦弱被同學欺負、父愛缺失原生家庭關系畸形、因性取向壓制內心情感,還被真心愛過的人背叛,第一次在被霸凌時勇敢反抗卻因暴力被判入獄,成長中的所有回憶幾乎都是痛苦不堪。
《月光男孩》的鏡頭以喀戎的主觀感受為主,再加上大量特寫注重展現人物的皮膚質感,令人感覺到時間在空氣中發酵。因此觀眾具有強烈的代入感,似乎跟著喀戎走完了一段充滿創痛、掙扎、苦悶的精神旅程。
當年《月光男孩》奪下奧斯卡最佳影片備受爭議,學院派認為這部電影有不可掩蓋的瑕疵,以及會被曲解為“政治正確”的討巧。但媒體仍對其不留余力的贊賞,因為它鼓舞、感動了許多曾有記憶創傷的人——我們終會被溫柔地接納。
每一個不同階段,都構成了我們獨一無二的自己。回歸與被拯救,無關于國籍、政治、性別,在藍色的大海與紫色的月光下,我們要正視與認可自己。
最終一切情感都化解在對自己往昔的回憶里。
2016 年《聚焦》,為新聞理想扳回一局。
《聚焦》是由托馬斯·麥卡錫執導的傳記劇情片,該片根據《波士頓環球報》中一篇新聞改編,以美國神職人員侵犯兒童的丑聞為背景,講述了幾位記者為了找出事實真相歷經艱難的過程。
《聚焦》沒有任何炫技的路線,臺詞也沒有什么金句,它就像一本講述記者從事調查報道的方法論。五位記者抽絲剝繭般查資料、懇求相關人員接受采訪,他們與看不見或看得見的反對力量抗衡。
即便是6年前的觀影感受,我仍記憶猶新——憤怒、悲痛,但也在新聞人堅持的職業理想中看見一絲光亮。
那些被侵犯的兒童因無人在意選擇忍氣吞聲,那些律師因害怕惹上麻煩選擇漠視,那些記者因怯于強權選擇沉默。但是,總有一群人堅持為遠方的哭聲發聲,堅持新聞人的操守和道德,堅持為良心而做踏上困難重重的正義之路。
而我們作為觀眾,在沉穩克制的鏡頭下,似乎也在跟著片中人一起認真尋求真相。或許社會默認了某種潛規則,但既然有在黑暗中摸爬滾打的人做榜樣,我們能看見光亮之后的新光景。
當然,除了以上七部電影,奧斯卡以往最佳影片的優秀也毫無爭議,它們都在盡力用藝術的方式展現真實的社會問題。但近幾年一個顯著變化是,奧斯卡近年來對非英語的電影態度更加開放。
比如今年獲得最佳國際影片的 《駕駛我的車》(往年還有《羅馬》《寄生蟲》《米納里》),獲得最佳劇本提名的挪威電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這也讓大眾對其獎項的專業度更為信服和尊重。
今年的奧斯卡主辦方還別出心裁,新增了“影迷票選最佳影片”和“奧斯卡摯愛瞬間”環節,前者將會在今年的奧斯卡上頒出,投票面向所有推特用戶。不難發現,奧斯卡對流媒體的態度從抗拒到迎合,正在力求變革挽回年輕人的心。
每一個電影頒獎不僅是獎勵,同時也是鼓勵電影人更好地創造,這已經成為一種文化、一種積極的電影方向。最后,家人們,一大波具有驚艷魅力的好片已經來襲,咱們可以抓緊時間看起來了,歡迎評論區和拳姐談談你最愛的電影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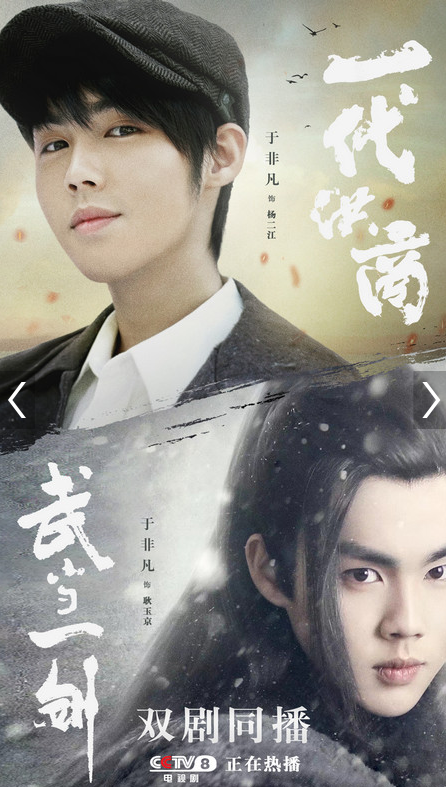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