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改編成影視作品是必然的,尤其是對于《人世間》這樣一個從六七十年代開始的故事,很多東西是拍不出來的。
不過電視劇的規模好像比我預想的要大。比如增加了類似李小璐0103 010的情節,表現知青的不幸,這是原著中沒有的。如果這些都能拍出來,我真的不明白為什么原著里很多看起來遠不如這個傷痕文學的情節拍不出來。
歸根結底,對改編影響最大的因素恐怕不是審查制度,而是編劇的個人喜好。
所以劇版里有很多改編讓我很困惑,我都快吐膩了。
包括周秉昆,鄭娟和周秉義,在內的主角們的性格與原著相比有了很多變化,但我只想說幾個最離譜的,不必要的,完全被丑化的角色。
其一是周蓉,這個我已經說累了。
在原著中,周蓉是自我的,而不是自私的。
當她還是個女孩的時候,她不顧一切地追求愛情,但當她成年后,她起死回生,腳踏實地。
她是一個追求精神幸福而不是物質幸福的人,但因為她足夠聰明,在日常人際交往中也能游刃有余。隨著時代的變遷,她越來越成熟,自然從不食人間煙火的女神變成了接地氣的美女。
關于她我之前已經單獨寫過了,就不細說了。
改編的思路是寫一個絕對的浪漫,在現實中被打死之后再與現實和解。
但是,馮完全有可能承擔這個責任,而不是周蓉;即使周蓉被要求做這個吃力不討好的角色,真的沒有必要讓她如此極端和令人窒息。
其二是孫小寧。
原著中,追到妹妹并沒有直接出現,也沒有名字。
出生在一個普通的東北工人家庭,在那一年的下崗潮中,周秉昆念著追上來追上去的情誼,特意請她到酒店工作。因此,她不想獨自去南方的深圳。
在深圳,她可能很努力,但畢竟,她“失去”了自己。她得了艾滋病,及時行樂,花完錢回東北了。她留下遺書,然后投河自盡。
過了很久,秉昆意外地得知一具如此殘破的女尸被打撈上來,而且從未被認領。他懷疑是追到妹妹了,但終究沒有告訴他。
那時候,即使是今天,追到姐姐,似乎也是一個貪圖享樂,自私短視的人,似乎不靠譜。
但是我很理解她。
其實該劇版本對當年東北的苦難輕描淡寫。原著里有很長很長的篇幅是關于工廠倒閉,工人下崗的,特別壓抑。我看的時候就想,普通人要走多大的運氣才能在這么冷的冬天活下來?
其實,要追到一個像我妹妹這樣的普通女孩,并沒有太多的選擇。
留在東北,和其他人一樣靠求人得到一份朝不保夕的工作,渾渾噩噩過完這一生,哪怕活一百歲,又有什么意義呢?
她走出了一條與眾不同的“拓荒者之路”,趁著年輕,及時行樂,揮霍無度,樂而不死。
姐姐在遺書里甚至寫了兩個滿足:沒結過婚,沒老公,沒孩子,不用擔心死;我沒有給父母和弟弟留下一點錢,但也沒有留下任何債務。她希望父母和哥哥不必為她的“離開”而悲傷,也不必為她的生活感到惋惜,因為她已經用以前賺的錢過了幾年富婆的生活。除了她不忍心丟盡節操讓人惡心,可以說那些年,她過著如她所愿的富婆生活,揮金如土。在最后一頁,她還寫道,在未來,普通人可能會在中國,生活得更好,肯定會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樣生活幾年!
并不是我很佩服她的做法,而是其實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沒有她那么極端(因為生活環境比她好),但大體心態都差不多。
img.com/origin/tos-cn-i-qvj2lq49k0/926c6ac43d1c466b95051d37dc1c76bd?from=pc">
然而劇中的孫小寧,完全變成了一個令人厭惡的綠茶小三,明知周秉昆有妻有子居然還不知廉恥地想拆散人家家庭……
這種為了狗血而狗血的改編,究竟有什么必要呢?
你哪怕說,為了表達當年大家都生活困難,孫小寧是貪圖周秉昆不僅自己是飯店經理、而且還有個當官的哥哥,為了過得好一點所以才想和周秉昆在一起,那樣我都能理解編劇的改編立意。
現在改成這樣,挺漂亮一個大姑娘,非要真心實意愛上一個既無外貌也無才華的中年已婚男人,圖啥?
就為了證明,作為男主角的周秉昆即便看上去再普通,也是魅力四射的,作為女主角的鄭娟即便再漂亮再善解人意,在婚姻中也會有危機感?
再到后面她跑去深圳了,終于走了和原著一樣的軌跡,然而卻堅持把第三者當到了底……
其三是吳倩。
梁曉聲在書中曾直言吳倩和于虹是“女權主義者”,當然,有點調侃的成分,畢竟那個年代,估計她們自己都不懂女權是個啥玩意兒。
吳倩和于虹見德寶懼內原形畢露,甚覺開心,相視壞笑。她倆是深藏不露的女權主義者,誰家老婆訓丈夫她倆都會歡欣鼓舞。
原著中,她第一次和國慶一起到秉昆家作客,一群年輕人閑聊,她所說的話,曾經很是震撼我。
當時是國慶講了一個故事,明明是男人失手殺死女人,在場所有男人反而都同情殺人犯,吳倩拍案而起:那個被殺的姑娘做錯了什么?
春燕雖然心里同情那個姑娘,卻因為一言不發的干哥哥秉昆也是男人中的一員而向著他說話。
吳倩又沖春燕嚷道:“一言不發就對了嗎?他如果是有正義感的,為什么不反駁他們三個?還有你!虧你也是女的!聽著他們三個男的一句句盡說我們可憐的姐妹的不是,你為什么也不反駁?”
當然,再往后看,她似乎也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普通女人。
是的,挺普通,雖然平時跟國慶也會因為家里的事吵架,可總體而言還是識大體的。
國慶患尿毒癥,沒錢治,于是臥軌自殺,留下了孤兒寡母,吳倩獨自拉扯女兒,可無論是國慶活著還是死了,她都沒有為了自己家的事去難為過秉昆。
(原著里臥軌的是國慶,劇里變成了趕超)
劇里的吳倩,成了一個升米恩斗米仇的小人,又是非要讓秉昆給國慶找工作、又是住著秉昆家里的房子不愿還……
當然,像這樣的人,現實里有很多,尤其是那個年代,實在是自己家里太難沒辦法,編劇非要拿吳倩來充當這種角色的代表……也行吧。
這三個女性角色,有的是主角有的是戲份很少的配角,但原著中各有各的不幸、也各有各的亮點,劇里統統變成了令人討厭的極品。
編劇王海鴿,明明也是女性,然而對待女性角色,反而還不如男性作者那么珍愛。
其實劇中很多女性角色,人格魅力或多或少都被削弱了。
比如郝冬梅,原著中的她,其實要比劇中聰慧得多。
在一開始周蓉為愛私奔后,周家人都不理解她,包括周蓉的哥哥周秉義,在收到周蓉的自白長信后雖然隱隱約約感覺自己理解了妹妹,可還是沒有徹底理解,是善解人意的郝冬梅,讓他真正認識了自己的妹妹,而且,當時的郝冬梅,一眼就看出了周蓉這段感情的問題所在。
雖然周秉義從小品學兼優少年老成,但是有時候他工作上遇到難題,還要郝冬梅來幫他出謀劃策。
但劇中郝冬梅身上這些亮點似乎統統不存在了,她似乎只是周秉義的妻子。
看上去好像只有鄭娟,劇版比書版更加堅韌了,或許因為這是殷桃演的,她看上去就有那么一股外柔內剛的勁兒。
可實際上,書里的鄭娟,也并不弱。
她看上去沒什么大追求,就算每天在自家灶臺打轉也能永遠都開開心心的,可是之所以如此樂觀,并不是因為她真的“有點二”,而是她繼承了母親的大智慧,恪守著最簡單而樸素的人生哲學,懂得知足常樂,永遠想得開。
原著中,駱士賓回來搶兒子,一直是跟周秉昆那邊“對接”的、把鄭娟蒙在鼓里,劇中卻是反過來,讓鄭娟直接對上曾經欺侮自己的強奸犯、把周秉昆蒙在鼓里,到后來為了周秉昆不惜去給駱士賓的妻子曾姍下跪……
這樣的鄭娟,表面看上去似乎更強了,實際上,就像劇中的郝冬梅完全只是周秉義的妻子、而不再是獨立的郝冬梅,劇中的鄭娟也完全只是周秉昆的妻子、而不再是獨立的鄭娟,她最大的亮點,完全沒有得到體現。
相比女性角色在改編中往往是魅力被削弱,男性角色卻更多的是渣男洗白。
比如,原著中最大的反派駱士賓,最大的渣男馮化成,劇中都變成了不乏觀眾喜愛的“好人”,簡直懷疑他們算不上給編劇塞了錢。
相比這兩位渣男變好,同為男性,原著中可以算是善人的水自流,反而被改編成了壞人。
為啥?
難道因為水哥的性取向跟那兩位渣男不一樣嗎?
水自流其實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角色,很難給他定義為“好人”,但要說他是壞人,那肯定也不是,所以我更傾向于稱他為“善人”。
他做的事,從法律和道德的角度來說,未必全都是好事,但就他個人處境而言,讀者還是可以感受到,他實際上有一顆善心,只是在特殊年代有很多身不由己。
因為這份善心,原著中在關于楠楠的問題上,他是完全站在周秉昆這邊的。
在此之前,大家都以為他跟水自流是一伙的,可實際上,根本不是。
劇中也提到,當年給鄭娟送錢,并不是駱士賓的主意,反而是原本與鄭娟和孩子并無關聯的水自流提出來的。
原著中,駱士賓是個徹頭徹尾的壞人,水自流自然不屑與他為伍,很看不上他。
而周秉昆則是個徹頭徹尾的好人,水自流相信,父母對孩子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楠楠由周秉昆撫養長大,絕對要比跟著水自流好。
所以,最開始還是水自流先提醒周秉昆,說駱士賓要回來搶孩子。
不錯,原著中水自流比駱士賓早一步回到東北,開了一家書店。
劇里變成周秉昆提議開書店了……
即便是在那個年代,水自流開書店也是不賺錢的買賣。但他有自己的原則,他認為無論在任何時代,人們都應該多讀書,讀好書,所以他開書店并不是為了賺錢。
書店的租金,是那些敬佩他的好兄弟們為他交的。
直到最后,水自流病逝之前,最放不下的,依然是這家書店,所以專門托人把周秉昆叫來,想要將書店交給他打理,但秉昆知道自己顧不過來,所以向水自流推薦了同樣愛書的邵敬文。
水自流告訴邵敬文,他開書店十幾年的體會是,中國人讀書的目的性很強,絕大多數人傾向于實用,這一點與西方人極不相同。在西方社會,不少人讀書是因為喜歡,正如他們因為喜歡花才買花,而不是認為花除了賞心悅目還有另外的用途。他為了考察人與書的關系到過農村,從前的農民還喜歡在窗前屋后種花,如今院子里有花的農家少之又少。農民對土地的用途也變得特別功利,即使桌面那么大的—塊地,也要種菜而絕不種花。他們把花完全看作生活中的多余物了。但是,那么一小塊地上生長出來的菜真的對他們一日三餐有什么特別的意義嗎?其實意義不大,也賣不了多少錢。他們種的菜往往吃不過來,喂豬了。豬多吃了幾口就能多長兩斤肉嗎?也不能,但親自喂給豬,眼看著豬吃掉,功利目的達到,心理就獲得了滿足。花有什么用呢?連家畜家禽都不吃。他說全中國都陷入功利主義泥沼,農民也不可能不焦躁,不受影響,而他們的功利目的又只有通過土地來實現,所以他們對土地變得急功近利,他們那樣做應該能理解。城里人樂意花買一本好書的錢,去買一塑料袋垃圾食品給自己的孩子吃,他難以理解。他說,他以前偏與現實較勁兒,凡助長功利主義思維的書,即使好賣也不進貨,結果繞了挺長一段彎路。什么教人炒股發財、長壽秘訣、八面玲瓏之類的書,只要好賣,那就進吧!
水自流當時對邵敬文說的這段話,我實在太贊同了,咱們中國人似乎的確是這樣,也是沒辦法,都是從苦日子里過來的,但是無論如何,真的不應該放棄讀書,不應該讓讀書變成一件純功利性的事情,我想這也是梁曉聲想對大家說的話吧。
遺憾的是,當年在水自流的病床前,曾姍嘴上承諾會把書店一直開下去,但水自流死后沒多久,她就把書店改成肯德基了。
老邵說:“你沒有什么對不起我的,是中國人太對不起書店了。中國都快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哪一個階層的人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中國人的閱讀率在世界上排名卻非常靠后。”
秉昆說:“水自流所以才希望能為這個時代做件好事。”
就是這樣一個頗有幾分風骨的水自流,在劇中幾乎變成了駱士賓的“走狗”……
搶楠楠這件事,他簡直比駱士賓還上心,服了,對周楠說出的那一番話,夠惡心人。
原本可以是挺討喜的一個角色,硬是惹得演員自己都自嘲說要把他另一條腿也打瘸……
總而言之,原著中很多充滿魅力的角色,到了電視劇里,統統都成為灑狗血的工具人,實在是可惜至極。
關鍵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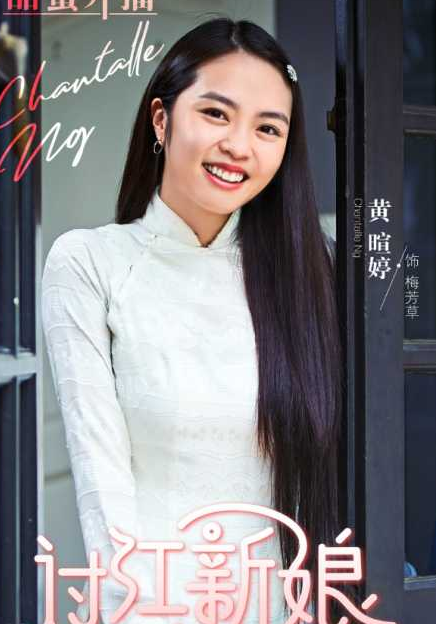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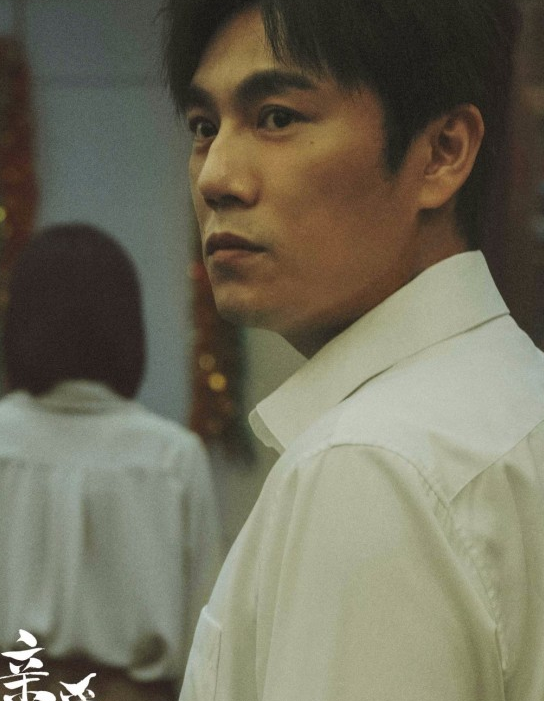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