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放映后被譽為“繼《釜山行》后又一亞洲神級恐怖電影”的《哭悲》,前兩天終于在流媒體上線了。
但大家期待了一年,看完之后的評價卻是統一的失望,并恨不得稱之為“亞洲第一大爛片”。
因為這部電影前期宣傳的所有恐怖,在片中只是靠血漿渲染得來,觀感除了惡心還是惡心。
可能它唯一保持的恐怖片調性,就是片中的女主角仍舊是一個耐看的美女。
恐怖片中必有美人,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成為了一個鐵定律。
《盧浮魅影》里奇詭卻艷麗的蘇菲瑪索,《著魔》里瘋癲卻又蠱惑人心的阿佳妮...每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神顏美人,一定有一部恐怖片代表作。
阿佳妮《著魔》
甚至于,再小眾的恐怖電影中也一定會出現一位讓我們眼前一亮的冷門美人,這種絕色是在愛情電影中都不曾見到的。
阿妮婭·皮艾羅麗《地獄》
那么,到底為什么恐怖片中經常有大美人?這些美人們的美貌,在恐怖片中又有著何種意義和作用呢?
今天,叔就跟大家盤盤由美人們塑造出的這種恐怖美學。
01
恐怖片中的尤物型美人:
展現暴力與欲望
大家仔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恐怖片中的美人風格是有規律可循的。
不同的美人臉蛋,會在故事中帶來不同的作用。
早期最典型的恐怖片美人大多是能爭奪人視線的尤物型。
《血與黑蕾絲》
她們的面龐上一律有著大量感五官,眼睛、鼻子線條尖銳深邃,金發碧眼,身材火辣,有著屬于大美女的銳利和端莊。
而將尤物型美人批量放進恐怖電影中的第一人,就是大家熟知的希區柯克。
希區柯克眼中的金發美人,是展現精神恐怖的最有利符號。
在50-60年代,恐怖片是壓抑下的男性幻想。
前一秒冰冷且遙不可及的美人們,后一秒就被窺視、被傷害,美女的恐懼、哀嚎,滿足了他心中的暴力與欲望。
當這些美人面越是美艷、性感,故事中的謀殺、地上的尖刀、墻上的小洞就越有沖擊性,越細思極恐。
不過,這樣的方式雖然能將恐怖電影中的尖叫和恐懼最大化地呈現了出來,但卻也帶著濃濃的厭女與摧毀意味。
《群鳥》的女主角蒂比·海德莉說,這是一部她拍過最恐怖的電影。
因為希區柯克會為了追求最真實的驚嚇,偷偷將戲中發狂的假鳥換成真鳥,甚至還會對她進行偷窺和追求。
而希區柯克卻說:“金發美女最適合被謀殺!想像一下,鮮紅的血從她雪白的肌膚上流下來,襯著閃亮的金發是多么美啊!”
受希區柯克的精神恐怖影響,充斥著驚悚、暴力與的意大利鉛黃電影,也成了尤物型美人的聚集地。
詹妮弗康納利《神話》
因為沒有審查制度限制,意大利鉛黃電影將美色與暴力的對撞發展到了另一個高度。
《陰風陣陣》
鮮明的色彩對撞,搭配微張的嘴唇、失焦的眼神,讓美人們的魅力不僅是性感的、冰冷的,還是孤僻的、神經質的。
鉛黃電影導演達里奧?阿基多的母親三部曲之《地獄》
02
恐怖片中的楚楚動人型美人:
蠱惑人心的受害者
除以好萊塢、意大利鉛黃為代表產出的尤物型美人外,恐怖美學中還有一種美人風格——楚楚動人型。
她們極具東方審美下的婉轉、纖弱形態,有著一張勻凈流暢的圓臉型,眉眼纖細,眼型可能是杏眼或圓眼,鼻型不筆挺但嬌小,像是東方畫作里的古典美人。
個人認為最美的一版貞子,仲間由紀惠
善于運用這種美的,是日本恐怖電影。
在50-70年代,日本恐怖電影還未發展成如今的暴力血腥風格,那時的恐怖片以古典的日式怪談為主。
新珠三千代《黑發》,講的是一個日版陳世美故事
這種古典志怪文學中的人物,與與我們的《聊齋》女鬼很類似。
美人們通常是怨靈形象,統統有著悲慘的過去+古典審美下無法讓人提防的可憐外貌。
嬌柔乖順、凄慘的八字眉,或無辜受害,或用外表來迷惑人心,伺機復仇。
《東海道四谷怪談》
在東方世界里,這種楚楚動人型美人完美契合了人們心中的恐怖要素。
女子柔弱,容易被傷害,需要復仇;東方的陰陽論中,女鬼又帶著最大的陰氣,容易幻化厲鬼。
高橋真唯,勻凈的圓臉
所以就算90年代開始,日本驚悚電影已經拋棄了古典怪談恐怖,這種美人風格也被留了下來。
《富江》
如今我們在恐怖片中常見的復仇蘿莉形象也屬于這一美人范疇。
短臉+3:1的顱面比+圓而大的眼睛,這種極其靠近嬰兒的面貌形態放在恐怖語境下,近乎于一個最完美的受害者。
《鏡中人》
韓國恐怖電影《人形師》
但也能在毫無防備下,帶來最無處可逃和癲狂的恐懼氛圍。
03
恐怖片中的瘋魔美人:
男人們到底多害怕被威脅
從五六十年代下的“看美人驚嚇”,到七十年代開始的“被美人驚嚇”。
直到現在,復仇的、癲狂的、惡魔式的美人形象,已經充斥在驚悚電影和恐怖電影中。
她們一律是以一種倔強和漠然的神態呈現出來,短中庭、稍近的眼間距和較短的眼裂,神情淡漠卻危險。
《魔女嘉莉》
梅根·福克斯在《詹妮弗的肉體》里斯飾演一名淫蕩又嗜血的女高中生,據說為了有真實性,這場火燒舌頭的戲是真燒,但她仍然要維持這種瘋魔之美。
恐怖片中的瘋魔美人越來越多,女性,也變成了恐怖電影中最受人矚目的部分。
與此同時我們發現,恐怖電影中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其實是與社會中的男性焦慮息息相關。
莫利·哈斯科在《從敬畏到強奸》提出女性威脅論:當女殺手還有女魔頭這類形象充斥銀幕,與女性在生活中獲取的經濟和社會權力同時發生,這也許并不是巧合。
70年代-90年代,恐怖片中的美人從“被害者”變成“加害者”的這個時間段,也是婦女在經濟、社會上的地位都逐漸提高的轉折點。
1973年的恐怖電影《驅魔人》,描述了一個12歲的小女孩被邪魔附體的故事。
隨后的《兇兆》、《魔女嘉莉》、《猛鬼街》,追求自由主義的婦女、性開放的青少年都成為了被魔鬼附身和殘害的目標。
《格蕾絲》、《孤兒怨》、《恐怖母親節》等恐怖電影中,倔強偏執的瘋魔人甚至都是母親的形象。
將女性角色妖魔化,似乎會讓男性觀眾短暫地從父權被威脅的焦慮里解脫出來。
但利用話語權去修改形象,就真的能阻止平等與意識覺醒嗎?
如今,驚悚片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大美人形象,她們不止要復仇,也揭示了父權統治對其的傷害和暴力。
尤物型美人不應再成為展現暴力的工具,楚楚動人型美人也未必就要成為被撕扯后的受害者。
當恐怖電影中的驚恐與瘋魔不再專屬于女性,那時,才會創造出最純粹的美學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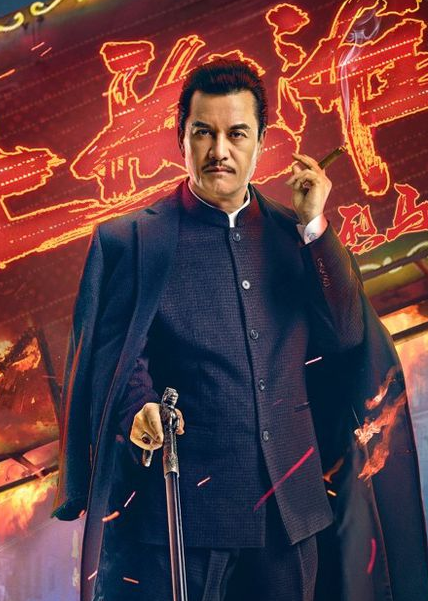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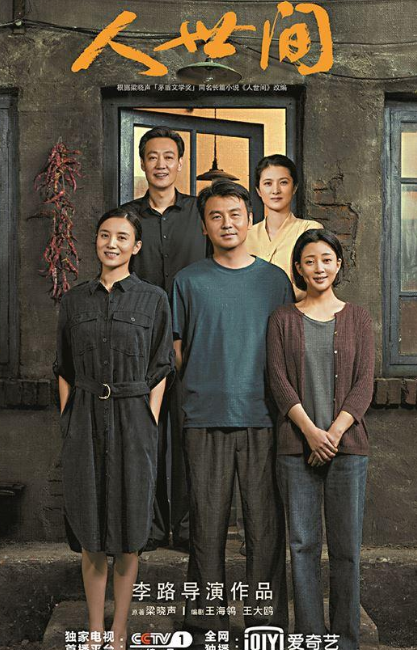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