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賢江
編輯 | 露冷
出品 | 貴圈·騰訊新聞立春工作室
* 版權聲明:騰訊新聞出品內容,未經授權,不得復制和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
4月24日《聲生不息》開播,來自中國香港的05后歌手炎明熹站上舞臺,演唱了一曲《蜚蜚》。那一刻,可能很多觀眾還沒有意識到,上一次登上湖南衛(wèi)視音樂綜藝舞臺、從香港出道的樂壇新人,是8年前在《我是歌手》奪得亞軍的鄧紫棋。
炎明熹在《聲生不息》第一期中演唱《蜚蜚》
過去8年,鄧紫棋成功打開內地市場,也幾乎遠離了香港樂壇,近年來只發(fā)行過一首粵語新歌《兩個你》。與她一樣經常出現(xiàn)在內地大眾視野中的香港歌手,還有王嘉爾,但他的韓國男團GOT7成員身份可能比“香港歌手”更為人熟知。操著一口流利普通話的王嘉爾,時至今日還沒有發(fā)行過一首自己的粵語單曲。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需要更多機會的香港年輕人紛紛北上,而大眾記憶中的“港樂”則越來越模糊。盡管近兩年隨著復古潮流飄然而至,“港風”不時撩動著人們的美好回憶,但對互聯(lián)網上的年輕一代來說,“港樂”二字更接近傳說,而不是現(xiàn)實。
除了少數(shù)港樂死忠,可能很多人已經很久沒聽過粵語新歌了。國內各大音樂App的年度榜單顯示,2021年內地最火的粵語歌,是陳奕迅20年前發(fā)表的《單車》。而更多的人,只會從諸如《大風吹》這些抖音神曲的“塑料粵語”里,感受港樂曾給大眾帶來的歡樂。
《聲生不息》有意成為跨時代的紐帶,把港樂和當下重新進行對接,讓更多年輕人感受到它的魅力。然而,綜觀輿論場里對這檔節(jié)目的討論,我們看到的更多是“情懷”二字。前6期節(jié)目,超過70%的歌曲發(fā)行于千禧年之前,其中發(fā)行于1990年代之前的歌曲更是占了一多半。老歌固然能滿足部分歌迷的懷舊情結,但也再一次強化了港樂“衰落”的一面。
01 離不開的“影視”
關于“港樂”,內地聽眾和粵語地區(qū)的聽眾有著不同的理解。在香港,“港樂”指的是香港交響樂團;而在內地,“港樂” 是香港流行音樂的簡稱,是“港片”和“港劇”的沿用。這從字面上體現(xiàn)了“港樂”與香港流行文化之間的“共生關系”。
對于這種“共生關系”,黃霑在論文中曾總結道:“香港的普及文化,如電影、 電視,及時地扶掖了港歌的興起與傳播,令其影響力遍及地球遠方角落,創(chuàng)造了劃時代的普及文化高峰。”
“普及文化”是“流行文化”的另一種說法。全球流行文化的發(fā)展,音樂、電影和電視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的。只不過,這一現(xiàn)象在香港娛樂圈尤其典型。粵語歌從市井走上前臺,從一開始就高度依賴影視作品。被譽為開啟當代粵語歌流行風潮的許冠杰,自1974年《鬼馬雙星》開始,最初的四張粵語專輯都是跟電影捆綁創(chuàng)作的結果。
1974年許冠杰在電影《鬼馬雙星》中飾演劉俊杰,并演唱同名主題曲
盡管發(fā)展到1980年代末,港樂已經不像早年那樣高度依賴影視作品存在,但張國榮、譚詠麟和梅艷芳能夠給內地受眾留下深刻印象,跟港片的帶動不無關系。在那個傳播渠道極不發(fā)達的年代,錄像廳和電視機成了香港文化向內地輻射的溫床,也因為語言的隔閡,只有港片和港劇才能夠讓港星的個人魅力在外埠獲得充分放大。
聽到張國榮的《當年情》和梅艷芳的《夕陽之歌》,必然會想到電影《英雄本色》;反之亦然。可能沒有多少人知道羅文發(fā)行了華語樂壇最早的“概念專輯”,但都聽過他為港劇83版《射雕英雄傳》演唱的主題曲《鐵血丹心》。又比如,假如不是因為周星馳的電影《食神》,《初戀》這首歌大概也不會出現(xiàn)在《聲生不息》的舞臺上。
這個趨勢一直持續(xù)到1990年代初的“四大天王”時代。如資深音樂人趙增熹在《聲生不息》中所說,1980-1990年代是港樂的黃金年代,“香港的音樂是輸出到別處的。”這種強勢也吸引了外埠歌手前來發(fā)行粵語專輯,張信哲當年就曾表示,發(fā)了粵語專輯才會覺得全體華人都在聽他的歌。
只是,彼時已是港片和港劇最后的輝煌:1993年,曾以古裝劇聞名的TVB開始引進中國臺灣版《包青天》;1996年,香港電影票房總收入腰斬,跌幅高達63%;同年,被戲稱為“港圈太子”的鄭中基發(fā)行國語專輯出道;第二年,王菲簽約EMI,之后再沒有發(fā)行過粵語專輯,而拍港片和港劇出身的梁詠琪,憑借首張國語專輯《短發(fā)》在音樂圈走紅。
1997年梁詠琪推出首張國語專輯《短發(fā)》
這一系列微妙的變化,預示著整個中國娛樂圈正在發(fā)生結構性變化,香港開始從中心位置走向邊緣,而裹挾其中的港樂,自然也難以獨善其身。
02 “偶像”消失
有個有趣的現(xiàn)象,今年參加《聲生不息》的香港歌手,80后集體缺席。雖然薛凱琪、鐘欣潼和蔡卓妍等80后香港歌手,出現(xiàn)在另一檔綜藝節(jié)目《乘風破浪》上,但毫不夸張地說,港樂跟受眾之間的關系,正是在80后這代開始斷裂的。
本來,80一代完全有可能繼承“四大天王”的衣缽,將港樂帶入新的歷史階段,卻沒想到,這代音樂人卻被幾乎一系列偶發(fā)事件“葬送”了。
千禧之交,80后開始在香港娛樂圈冒尖。16歲出道的謝霆鋒,憑借帥氣的相貌和不羈的個性,一度成為港樂的超級偶像,一年發(fā)行7張唱片,張張大賣。比他小兩歲的陳冠希,一度被視為港樂新偶像,改玩說唱之后也是風生水起,還因為參演《無間道》和《頭文字D》等影片而人氣急升。2001年出道的女子偶像組合Twins,不但風靡全港,在華語樂壇也能跟S.H.E.分庭抗禮。容祖兒則從2003年開始登頂香港樂壇,完成了天后的交接。
2003年容祖兒擔任謝霆鋒演唱會嘉賓
流行音樂始終是年輕人的市場,年輕一代所表現(xiàn)出來的活力和個性,決定了流行音樂市場的發(fā)展方向。玩搖滾的謝霆鋒和玩說唱的陳冠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為港樂注入新的個性,Twins則填補了港樂缺乏高人氣女子組合的歷史。如果一切能順利發(fā)展下去,港樂或許將會是另一番面貌。
2002年,謝霆鋒因為“頂包案”入獄半年,此后便轉到內地拍戲,音樂事業(yè)受到極大影響。他上一年才發(fā)行了被樂迷視為“神專”的《玉蝴蝶》,眼瞅著有望邁上新臺階,卻戛然而止。2008年,“艷照門”事件后陳冠希宣布退出香港娛樂圈,張柏芝和Twins的演藝事業(yè)也遭到沉重打擊。
雖說21世紀的香港樂壇因為陳奕迅和楊千嬅等的歌手崛起而不乏佳作,但80后當紅偶像的斷檔,無疑給香港樂壇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
在音樂產業(yè)里,“偶像”是維系青少年市場的紐帶,也是維持市場熱度的關鍵。在黃霑看來,香港樂壇之所以在張國榮和梅艷芳退隱之后仍然保持活力,適時捧出“四大天王”是重要的一步。張國榮也說,因為有黎明和劉德華撐住香港樂壇,日本仔一直抬不起頭。
然而,21世紀前十年,隨著偶像一個個崩塌,香港樂壇也變得黯淡無光。相反,周杰倫和五月天等外埠新人倒是來勢洶洶。2005年,香港的音樂頒獎禮還專門為臺灣偶像設置了“唱跳歌手獎”。再往后,韓流又來了——Spotify公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自2018年開始,BTS連續(xù)四年成為香港最高播放量組合。
03 成敗皆是TVB
說到港樂,就不得不提TVB(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1982年,TVB和旗下的唱片公司華星聯(lián)合創(chuàng)辦“新秀歌唱大賽”,梅艷芳成為首屆冠軍,拉開了港樂黃金時代的序幕。隨后,擁有梅艷芳、張國榮和羅文等巨星的華星唱片,在TVB的支持下,撐起了樂壇的半壁江山。
1982年,梅艷芳獲第一屆新秀歌唱大賽冠軍
1980年代既是港樂的黃金年代,也是TVB電視劇和綜藝節(jié)目全面開花的時代。黃日華、翁美玲主演的《射雕英雄傳》創(chuàng)造了史無前例的收視紀錄;“十大勁歌金曲”成為香港樂壇的風向標,也催生了很多熱門話題——比如1989年發(fā)生的《夕陽之歌》和《千千闕歌》之爭。
在那個年代,歌手們沒有太多選擇,要么簽TVB,要么配合TVB。這一情況,直到2010年才有所改變。當時,張學友接受了亞視的粵語采訪,這居然成了坊間大事。很多人因此才知道,原來歌手們選擇了TVB,就不能接受其他電視臺的粵語訪問。
張學友的選擇,實際上是唱片公司和TVB博弈的結果。因為四大唱片公司(環(huán)球、華納、索尼、百代)等組成的香港音像聯(lián)盟(HKRIA)在版稅問題上跟TVB無法達成協(xié)議,HKRIA方面不讓旗下歌手參與TVB的節(jié)目,而TVB則以封殺反制。
結果是,謝安琪等正處于事業(yè)上升期的歌手,失去了本地大媒體的支持,而TVB則開始力捧自己人。2012年年初,林峰獲得“十大勁歌金曲”的金曲金獎,惹得知名音樂人陳輝陽怒批“樂壇已死”。然而現(xiàn)實情況是,因為四大唱片公司歌手的集體缺席,TVB也著實沒有什么人可捧了。
唱片公司抱團跟TVB正面沖突,這樣的情況,在21世紀之前是難以想象的。在電視統(tǒng)治客廳的時代,沒有電視臺播放MV、不參加電視臺的綜藝節(jié)目,歌曲就沒辦法“入屋”,歌手就沒有出路。21世紀后,隨著互聯(lián)網的興起,電視渠道受到了巨大的沖擊,林一峰等個別歌手靠著新媒介的支持,居然實現(xiàn)了收支平衡,唱片公司也因此有了跟TVB叫板的勇氣。
林一峰在香港娛樂電視頻道ViuTV演唱《the best is yet to come》
HKRIA對TVB不滿,也跟行業(yè)不景氣有關。因為唱片銷量不斷下滑,唱片公司越來越依賴歌曲授權維生,不得不想辦法虎口奪食。HKRIA和TVB博弈,受傷害最大的只能是港樂。上個十年的動蕩余波未盡,新十年又以版權糾紛起步,最終只能讓香港音樂圈雪上加霜。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2010年之后港樂曾呈現(xiàn)的混亂,跟這場版權糾紛有直接關系。2013年開始,TVB把“十大勁歌金曲”改成評選20首,原本就被批評像“太公分豬肉”的音樂頒獎禮進一步“注水”,公信力盡失。2018年,古天樂憑借半首歌曲(與謝安琪的合唱歌曲《(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和浴室》)獲得叱咤樂壇“最喜愛的男歌手”。作為一個由網民票選投出的獎項,這其實是新媒介的年輕受眾,用鼠標來發(fā)泄自己對于樂壇現(xiàn)狀的不滿。
04 “港樂”的另一面
開播至今,《聲生不息》在輿論場里引發(fā)了不小的反響,并且從播放量上便可看出節(jié)目企劃的野心。作為一檔面向大眾的綜藝節(jié)目,《聲生不息》的選歌充分體現(xiàn)了大眾的趣味,所以才能引發(fā)共鳴。
不過,從更熟悉港樂的廣東地區(qū)媒體和一些港樂愛好者的反饋看,《聲生不息》所展示的港樂和現(xiàn)實之間,仍然存在著很大的“缺口”——微博上,港樂迷們?yōu)椤堵暽幌ⅰ吠扑]了大量的“遺珠”。
“缺口”并不是現(xiàn)在才有。作為一種方言音樂,粵語歌有著天然的傳播門檻,而高度依賴港片和港劇對外輸出的港樂,很難面向外埠受眾展示本身獨立的、音樂性的一面,于是就造成了一種無法避免的認知鴻溝。
一方面,大眾認為港樂“輕原創(chuàng)”,另一方面,大量優(yōu)秀的原創(chuàng)作品卻無人賞識。羅文的《激光中》是華語樂壇最早的本土原創(chuàng)說唱歌曲,林慕德的作曲和編曲在當時堪稱一絕,然而這首歌在QQ音樂上的評論量是零。林慕德的另一首作品——陳百強的《創(chuàng)世紀》,被一些樂評人認為不亞于同期的改編作品,在音樂App上也評論寥寥。此外,又有多少人聽過倫永亮為許冠杰創(chuàng)作的《擦鞋仔》——盡管它被認為是一首融合了時髦曲風和本土文化的佳作。
許冠杰《擦鞋仔》MV,“擦鞋仔”翻譯成普通話為“馬屁精”
1990年代起,雷頌德、譚國政、C.Y.Kong、陳光榮等新一代創(chuàng)作人為港樂帶來了新氣象,1995年的原創(chuàng)歌運動,也為本土青年才俊創(chuàng)造了更多的發(fā)揮空間。1990年代末,港樂又涌現(xiàn)出了陳輝陽、郭偉亮等創(chuàng)作新銳,港樂基本原創(chuàng)化。甚至,在陳少琪等音樂人看來,九十年代的香港樂壇比八十年代更好。
然而,“四大天王”那么火,也沒有改變粵語區(qū)之外的大眾對于港樂“輕原創(chuàng)”的印象。隨著香港娛樂圈整體衰落,港樂也越來越難以傳播到外埠的大眾市場里,而漸漸變成了一種圈層文化。
王菲的粉絲為C.Y.Kong的作品津津樂道,但大眾只知道陳小霞、中島美雪和《執(zhí)迷不悔》。
黎明的粉絲們把雷頌德視為“怪才”,他的電音舞曲全是原創(chuàng),但大眾對黎明的印象始終停留在《今夜你會不會來》和《夏日傾情》。陳奕迅的粉絲把郭偉亮稱為“永遠的神”,但陳奕迅的歌,很多人可能只聽過《十年》和《愛情轉移》,如今再加一首《孤勇者》。
實際上,哪怕是在21世紀初的“多事之秋”,港樂仍然有大量的優(yōu)秀作品涌現(xiàn)。香港樂評人馮禮慈認為,港樂從2005年開始出現(xiàn)了復蘇的跡象,陳奕迅、王菀之和楊千嬅等歌手在那些年都有很多好歌好碟。然而內憂外患之下,此時的他們已經很難突圍了,而方大同等80后新人甚至干脆放棄了粵語歌市場。當他的國語歌曲在《聲生不息》被唱響,我們聽到的更多是港樂的無奈。
《聲生不息》中單依純演唱方大同作品《三人游》
香港的本地市場太小了,如果不能夠持續(xù)輸出,最終結果只能是自娛自樂。而21世紀前十年發(fā)生的各種事件甚至將“自娛自樂”的空間都摧毀了。走投無路的唱片公司,只能靠簽模特和演員求生。這當然是一種急功近利的表現(xiàn),但也是造星體系崩塌之后的無奈之舉。固守這樣一個彈丸市場,唱片公司還能有多少選擇?假如香港樂壇能像過去一樣,源源不斷地捧出超級巨星,林峰也不至于將近30歲才當歌手。
經過多年的討論之后,業(yè)內已經能夠正視這樣一個事實:香港娛樂文化當年的火爆,更多得益于內地和臺灣經濟發(fā)展的相對落后。2012年,在一檔探討香港樂壇現(xiàn)狀的電視節(jié)目里,資深經紀人郭啟華說:“從前我們確實是文化輸出的重鎮(zhèn),香港是一個很重要的樞紐,但現(xiàn)在別人越來越強大了,聽自己的歌就夠了,為什么要聽你的歌呢?”
這正是港樂需要面對的核心問題。在周邊市場不斷發(fā)展的情況下,香港樂壇卻由于各種因素影響而步履蹣跚,最終只能眼睜睜接受被邊緣化的現(xiàn)實。好在這些年,“港樂”漸漸呈現(xiàn)出一種獨特的氣質:它只不是一種潮流,更是一種根植于香港城市生活的大眾文化。大眾文化不會消失,只會沿著另一個維度重新編織,并最終找到一個新的出口。
近年來,港樂新生代的崛起證明了這一點。在傳統(tǒng)電視渠道已無力支撐港樂發(fā)展的情況下,以網絡為主陣地的新媒介承擔起延續(xù)香火的重任。異軍突起的ViuTV,借助互聯(lián)網的力量,捧紅了男團MIRROR,為港樂帶來了新偶像的同時,也讓年輕人重新聚焦香港樂壇。
2021年MIRROR《WARRIOR》MV
更讓人驚喜的港樂新一代創(chuàng)作者的崛起,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吸引著年輕聽眾,也改變著港樂的發(fā)展。Spotify發(fā)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2021年香港播放量最高的十首歌,全部是本土歌手作品,其中唱作歌手林家謙一人占了五首,他的粵語專輯《MAJOR IN MINOR》還位居香港全年最高播放量專輯第一,在他身后是賈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和艾德·希蘭(Ed Sheeran)。
唱作歌手霸榜的情況,別說在港樂,在整個華語樂壇都很罕見。除了周杰倫,你可能很難再想到別人,而林家謙歌曲在香港地區(qū)的總播放量甚至超過了周杰倫。2022年,更年輕的唱作人湯令山橫空出世,他因為給姜濤等港樂新偶像創(chuàng)作而受到關注。盡管他們的影響力還只停留在香港地區(qū),但這些年輕歌手的存在提醒我們,伴隨著大環(huán)境的起落,港樂正處在一個新的蓄力階段,它和它代表的大眾文化始終保留著根基,不斷傳承,生生不息。而我們,也是時候換一個角度去看待港樂了。
(來源:騰訊新聞)
*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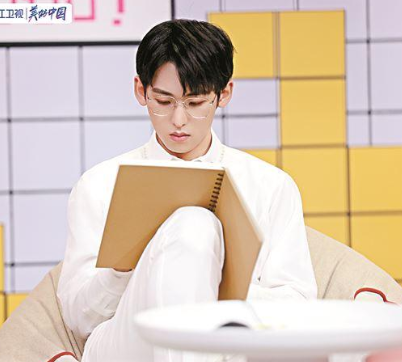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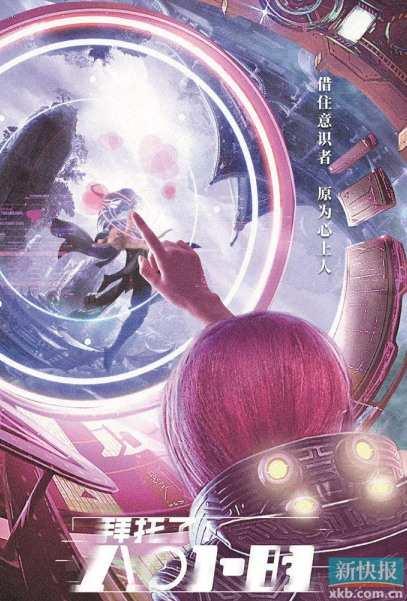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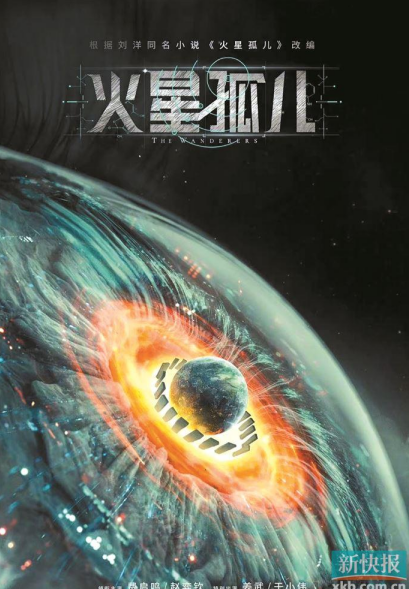







 營業(yè)執(zhí)照公示信息
營業(yè)執(zhí)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