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申明:本文為@影吹斯汀 獨家原創稿,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抄襲or轉載,違者必究!】
最近,導演陳可辛在海外成立泛亞洲制片公司,進軍亞洲流媒體市場的新聞,成了內地影視圈的熱點話題。
這家新公司名為Changin’ Picture,合作的對象是韓國、泰國、中國香港等亞洲多國多地的導演,旨在獨立開發、制作影視劇。
 【資料圖】
【資料圖】
因為擁有從亞洲渠道籌集的大量啟動資金,前期無需求助大平臺的投資,也不受限于外部的制作許可和編輯權限,項目完成后直接賣給Netflix等流媒體,目標受眾在亞洲乃至全球范圍。
首批將推出的五個項目中,有兩個是韓國劇集,均改編自新世代人氣漫畫。
《ONE: High School Heroes》主打熱血動作,涉及校園霸凌和青少年犯罪情節。另一部《2班李喜舒》則是耽美題材。放在當下內地的審查環境,都難以幸存。
還有兩個項目與華語影視相關,且有大腕加盟。
一個是甄子丹制片并主演的奇幻動作劇集《敗北之人,隱藏大師》(Outright Loser, Hidden Master)。
一個是由陳可辛本人執導,章子怡主演,預計明年開拍的驚悚懸疑劇集《醬園弄殺夫案》(The Murderer)。
2016年陳可辛就將此劇立項,但一直未能啟動。劇本改編自1944年發生于上海的真實事件,圍繞一個被指控謀殺并肢解丈夫的女人展開故事。
以陳可辛的話來回應這一系列大動作,是《魷魚游戲》《寄生蟲》等韓劇韓影的成功出海,讓他看到非英語作品的全球市場潛力,不禁躍躍欲試,想要“拍全世界都看的中文劇”。
但聯想到大陸影視圈目前蕭條又嚴苛的現狀,很難不把他新公司“泛亞洲、環大陸”的事業新藍圖,理解為名導內地拍片多次受挫后,疑似放棄內地市場的總路線變更。
盡管他經常被業內人士稱為“最懂中國大陸的香港導演”。
結合陳可辛北上拍片的履歷,我們大體可以明白“懂大陸”的評價至少有兩層含義。
一是肯俯下身去,觀察、迎合廣大觀眾的審美趣味和情感需求,講述有現實精神的中國故事,探索市場新方向,培育新人才。
過去這十余年間,陳可辛拍出了主打通俗大眾的《中國合伙人》《親愛的》;嘗鮮了歌舞片《如果·愛》、風格化的《武俠》與大制作古裝戰爭片《投名狀》;挖掘扶植了曾國祥(《七月與安生》《少年的你》)、許宏宇(《喜歡你》《一點就到家》)等新導演。
可以說,是一個了解產業,也愿意了解觀眾的全能型電影人。
《投名狀》劇照
二是肯低下頭來,平衡、消化各方的指令和壓力,在安全范圍內,保持一定的自我表達。
比如在歷經投訴、刪減、改名、延期上映等風波后,保質交出以女排精神側寫時代變遷的主旋律電影《奪冠》。
不過,在主旋律愈發走強、題材集中化的這幾年,想要一邊做任務,一邊做自己的陳可辛,還是顯得有些落寞、不順。
被金雞獎授予最佳影片的《奪冠》,是一部政治過關的電影,但8億出頭的票房、平平的觀眾反響,以及映前的一系列挫折,還是讓從業三十余年的陳可辛有些疲倦,直言這是他拍片經歷里最難的一部戲。
《奪冠》的拍攝經驗,讓他“得到了一些結論”
而另一個他早就想拍(2015年開始籌備),也已經完成拍攝(2019年殺青)的大項目——聚焦網壇名將的體育傳記片《獨自上場》(原名《李娜》),則默默沒了消息,內地上映恐無望。
陳可辛在《獨自上場》片場
從這些“挫敗”來看陳可辛近幾年的創作表現,其實比不上移植港片經驗,把愛國商業片玩得風生水起的徐克、林超賢、劉偉強等北上同僚。
如今,他跳出大陸單一市場和審查的束縛,轉而面向創作更自由,受眾更廣闊的泛亞洲,也不足為怪了。
不過,陳可辛的這次“出走”,僅僅是因為他近幾年趕不上趟、受挫太多、心灰意冷嗎?
要知道這不是陳可辛第一次轉換陣地了。
妻子吳君如在《金雞》里的經典臺詞“要生存就要變通”,或許才是他一切行動的真實注解。
陳可辛:沒有使命感,首先捍衛生存權
某種程度上,陳可辛的職業軌跡,基本與香港、內地乃至亞洲電影市場變遷的幾個關鍵節點同步。
嗅覺敏銳、思維開放的他,也一直感知、順應著時代風向,或加速前進,或及時調轉船頭。
1962年出生于香港,12歲隨家人移居泰國的陳可辛,求學于美國,曾計劃留在好萊塢打拼。但80年代,香港電影新浪潮的崛起,讓他看到本土制作與新導演上位(徐克、許鞍華等)的希望,于是果斷回到香港。
陳可辛與曾志偉
在片場與制片公司的各個崗位磨礪了幾年后,他聯手曾志偉等人創立UFO電影公司,拍攝了一批主打本土中產市場的新都市電影,如《雙城故事》《新難兄難弟》《金枝玉葉》,制造了一波市民電影潮流。
上世紀90年代,陳可辛雖沒有直接參與到兩岸三地的合拍小浪潮(陸港合拍、臺灣投資的一系列電影《活著》《霸王別姬》《新龍門客棧》等),但還是在香港本土,捕捉到97變局前的時代氣候,拍出了一部關于離散、漂泊與欲望的經典愛情片《甜蜜蜜》。
1998年,他轉陣好萊塢斯皮爾伯格的夢工廠工作室,試水了一部愛情片《情書》。因結局版本與制片人存在分歧,意識到美國的大廠制“堅不可摧”,“好萊塢的發行制度就像巨怪一樣已經刻進了DNA很難產生變化”,遂再度返回香港。
那時,香港本土電影已經一落千丈,他便起了整合亞洲電影資源的心思,成立了電影公司Applause Pictures,先后與泰國、日本、韓國以及新加坡的制作單位合作了《晚娘》《春逝》以及《見鬼》等電影作品。
而這也是現今更為系統的泛亞洲影劇計劃的早期形態。
進入21世紀,陸港簽訂CEPA(《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合拍片浪潮正式開啟。
2005年,陳可辛應勢北上,成為第一個在北京成立工作室的香港導演。他的合拍首作《如果·愛》,率先嘗試華語歌舞類型,票房雖不甚理想,但在兩岸三地各大華語頒獎禮上風光無限,如今回看,也是佳作。
2007年,聯合李連杰、劉德華、金城武三位巨星打造的古裝戰爭片《投名狀》,讓他成為繼張藝謀(《英雄》)后,第二位步入兩億票房俱樂部的華人導演。
2009年,陳可辛與黃建新在北京成立“我們制作”。同年,“我們制作”與博納于冬共同創立了“人人電影”,歷史題材大片《十月圍城》是當時的主推項目。
2013年,《中國合伙人》應聲而出,拿下5.8億票房,位列年度票房榜第七,是他北上以來市場表現最好的一部。
此片也再度證明了陳可辛體察時代、摸準市場、平衡商業與藝術的能力,正式奠定了他在商業現實題材領域的成功,為后續尖銳的拐賣題材電影《親愛的》,與政治分量極重的主旋律體育片《奪冠》鋪路。
由此可見,陳可辛既是華語電影圈業態變遷的見證者,也是最積極的參與者之一。
當年應勢北上,如今投身泛亞,都是時局變幻時,因勢利導的先手。
國慶期間,一起和陳可辛刷屏娛樂新聞版面的湯唯,就明顯受益于興起的泛亞洲影視交流合作。
憑借《分手的決心》榮膺釜日電影獎影后桂冠的她,已經成為首個達成韓國影壇“三小滿貫”的外籍藝人。從資源到成績,都非常出色。
在韓國擁有個人作品展
陳可辛的徒弟,也是老友曾志偉之子曾國祥,也合作了奈飛(Netflix)等國際團隊,聯合執導了中文科幻大IP《三體》的劇集版。
釜山電影節上,備受關注的影帝梁朝偉,也表示“看著韓國演藝界很高興”,透露正在接洽美國劇集。
除了華語影人,在更大的亞洲范圍內,各個國家之間的影視合作也在不斷增多,試圖實現更高層面的共贏共榮。
在年中的戛納電影節上,是枝裕和與樸贊郁領銜的亞洲影人團隊,就是明證。
前者用韓語片《掮客》,把韓國名演員宋康昊送上了戛納影帝的寶座。后者則以《分手的決心》拿下最佳導演獎,并讓中國演員湯唯閃耀銀幕。
能夠生存、可以發展,是電影及其他各行各業的安身立命之本。
假如咱們的內地市場和創作環境再這么繼續下去,人才出走、資金外流的情況可能會以各種形式出現。無關政治,就是市場行為使然。此前受益十余年的內地電影市場,也不得不面對、接受新階段和新局面了。
(文/mo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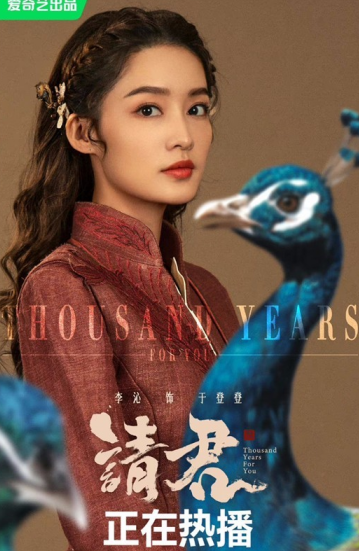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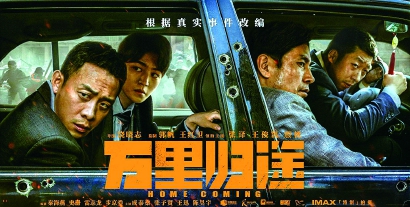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