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人世間》中的女性形象——曲秀貞、金月姬、鄭娟、周蓉
大戲《人世間》自開播以來,好評不斷,究其原因除了作者梁曉聲為原著苦心經營八年之外,與編劇王大鷗、導演李璐的深厚功底分不開。劇中殷桃、雷佳音、宋佳等實力戲骨還原新成立到改革那一段艱苦歲月。
在劇中除了思考“文革”、知青、改革等歷史話題,《人世間》還融入了私生子、同性戀、婚外情、反腐、整容等一系列“時尚”元素,其中對“社會人”等新鮮詞匯的解讀更是精彩回應了當下流行文化風向,顯示出強烈的現實性與現時性。從女性的角度來看,劇中深入探索世道人心,以及對不同時代、身份、階層女性的整體理解。
曲秀貞
曲秀貞是“紅一代”的典型,她十五六歲就參加革命,是個不折不扣的“紅色老太太”。作為子,當丈夫在特殊時期被“靠邊站”前途未卜之際,曲秀貞選擇背棄“革命”,拒絕“劃清界限”,以子的身份同丈夫站在了一條戰線。曲秀貞因“一家三位抗日烈士”而自豪,對黨始終忠誠。
曲秀貞的社會角色帶有強烈的時代印記,革命浪潮吞噬了女性的自我屬性,打“右派”的行為是她忠于革命/權力的體現,而扶助周秉昆則是老之將至幡然悔悟,贖罪心理驅使下的向善行為。
從曲秀貞身上,我們可以看出曲秀貞這個人物飾演“好人”的可變性與性,引發人們重新思考“好人”的評價立場與價值標準。
金月姬
金月姬是曲秀貞的同代人,她十九歲入黨,具有東三省地下工作者的老資歷。金月姬將革命視為崇高的象征,認為“革命不是交易,人不應該向組織擺資格,和組織討價還價”。如在劇中因為蔡曉光事件,而讓其耿耿于懷。
革命思想浸染下的女性具有濃厚的階級意識,這就意味著她們主動從自我走向群體,放棄個體話語而融入集體聲音。階級意識導致了女性現代意識的缺失,自由平等理念的匱乏。受根深蒂固的階級觀念影響,金月姬雖然接受了女兒郝冬梅的婚姻,卻從未登過親家的門,在她看來:“如果不是由于‘文革’,她就不會與普通工人之家成了親家,還是光字片的工人之家。”
劇中有個重要的情結,在金月姬知道秘書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周父帶的茶葉和周秉義帶來的南方特產又返送給周家之后,郝冬梅與其爭吵過程中說出了:“就像您今天安排黃秘書去人家家送東西,你們是高高在上,說風就是風說雨就是雨,但是你有沒有想過,您的這些安排,不就等于在跟別人強調,你們和他們的差距嗎,何必呢?”。此情此景,革命話語退場,階級鴻溝開始顯現。
當郝冬梅父親去世之后,作為家庭中的岳母,金月姬這位老革命“挺拿勁兒”,不惜以自己的“革命”資歷為女婿的仕途謀求發展。
在劇中導演在革命敘事中有意淡化了女性的“革命”身份,突出了女性的“家庭”(個人)身份,反思革命/權力意志籠罩下“人”的堅守與妥協。
鄭娟
《人世間》中的“好女人”是恪守“美德”的“民間的天使”,以鄭娟為典型。“民間的天使”首先具有“民間性”,她不必有精英特質,不必有高學歷高智商。“民間的天使”還具有“神性”色彩,必須有“天使”的溫柔博愛、善解人意。梁曉聲筆下的鄭娟,既沒有郝冬梅的高干子女背景,也沒有周蓉的高學歷,是美貌、溫馴、博愛的“天使型女性”,也是恪守“美德”的典范。
《人世間》中,女性對“美德”的恪守首先體現在成為“賢良母”的自覺。這種自覺容納了女性的善良、堅強、感恩、進取、寬容等諸多“美德”。鄭娟將自己視為“天生的賢良母”,擁有“賢良母”的高度自覺。當周秉昆的母親變成植物人,周家陷入困境,鄭娟不顧流言住進周家,悉心照料周母,有擔當。
鄭娟以“小人物”自居,認為社會政治一類的“大事情”不該由“小人物”負責。雖與政治絕緣,鄭娟依然具有社會屬性,“民間的天使”正由于其“民間性”決定了其世俗性的一面。鄭娟的文化程度低,不關心政治,但對人性、人心的見解獨到,對日常生活的感知細膩。她以“性格”喻“皮膚”,勸說周秉昆改變性格,對人熱情以實現事業的上升,在她積年累月的“民間”認知體系里,“性格像皮膚,大太陽下曬久了誰都黑了,關在屋里一年半載的誰都會變得白了點兒。皮膚黑了白了,只要心沒變,還是一顆好人心,那就還是先前那個好人”。鄭娟用她的“性格皮膚理論”贏得了丈夫的認可,成為周秉昆的“枕邊師”。
周蓉
革命倫理與家庭倫理之外,《人世間》還從自由倫理的維度探討女性作為“人”的話語實踐。“不自由,毋寧死”的周蓉是《人世間》中眾多女性中“知識女性”的代言人。蔡曉光眼中的周蓉是“特殊的女性”,“總希望超越普通人生”。周蓉眼中的自己則融合了眾多文學作品典型人物的特質,將“艾絲美拉達的沒心沒肺”“卡門的任性”“馬蒂爾德的叛逆”“娜塔莎的純真”“晴雯的剛烈”“黛玉的孤芳自賞式的憂郁”“寶釵的圓通”集于一身,個性十足。
周蓉的“任性”主要體現在“愛情至上”的人生信念。她為了追隨詩人馮化成,不顧困頓辛勞,不惜與家人不辭而別,遠赴貴州偏遠山區,一心守護愛情“信仰”。“文革”背景下,周蓉“離家出走”的意義顯得非同尋常。受愛情驅使,周蓉對“現行反革命”馮化成不離不棄,這意味著她與主流意識形態的“決裂”,也意味著“政治清白”的喪失。事實上,周蓉以“叛逆”之舉捍衛了“自由”的神圣,呵護了“正義”的微光,承載了作者對“精英女性”的期待。
周蓉無疑是“積極自由”的踐行者:她在貴州艱苦的環境中仍然不忘知識分子的責任,希望寫一本紀實性的書籍,以引導大眾對于國家的認知;她在北大讀書時期,發起“好學生的好”與“好人的好”辯論,實則反思“文革”;她對和馮化成之間無疾而終的愛情“無怨無悔”。從革命的“無怨無悔”到青春的“無怨無悔”再到愛情的“無怨無悔”,梁曉聲力求于苦難中發掘甘甜,“無悔”心態背后含有對個體命運的接納與認同,即使個體命運處于時代或社會的掌控之中。“知識女性”追逐自由的理性和獨立在周玥身上體現為國族意識的淡薄、自由意識的濃厚,以及價值判斷的自主與人生選擇的務實。
關鍵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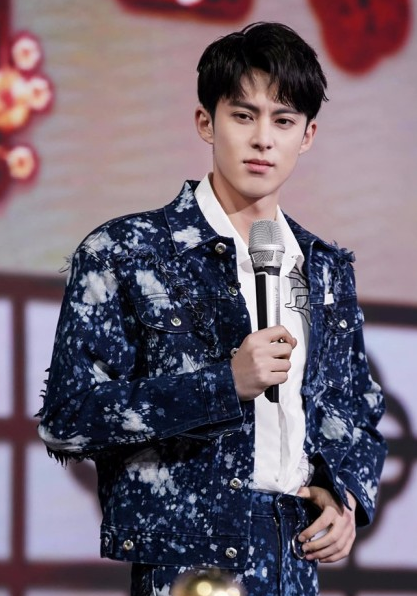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