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莊珈人
編輯 | 露冷
出品 | 貴圈·騰訊新聞立春工作室
* 版權聲明:騰訊新聞出品內容,未經授權,不得復制和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
王濛今年38歲,退役8年,參加的上一屆奧運會還是在2010年。她兩年前卸任了國家短道速滑隊教練組組長一職。她不能說流利的英文,身世背景不能提供談資,也沒有那種可以換化為偶像的外形。她站在2022年冬奧會賽場外,和谷愛凌、羽生結弦等運動員一起,成為北京冬奧會最耀眼的明星。
有人稱她為北京冬奧會“吉祥三寶”,最早出圈的金句“我的眼睛就是尺”,正是由她在直播間喊出。她的解說風格如此鮮明,咆哮、拍案、直言不諱、激情指點,也在最需要最專業判斷的時刻,作出準確詳盡的說明。
每屆奧運會都會誕生自己的明星。每個明星都能創造自己的時代。一個已經退役的運動員,依靠個人魅力,獲得觀眾如此廣泛的喜愛,這并不多見。谷愛凌和羽生結弦的傳奇正當時,“濛時代”已過去將近十年,但這一點都不妨礙這位運動員,保持著快樂、甚至“滿身頑性”,和觀眾保持著情緒的共振。
王濛在2月5日第一場解說就引起了關注。“德云社在逃相聲演員”,這是人們對這位前頂尖運動員的第一印象。隨后,隨著賽程競爭越來越激烈,她提供的情緒價值和專業價值,也就越來越不止于好笑了。
短道速滑男子5000米接力半決賽的這個晚上,她“嗔怪”觀眾:“別總想著決賽的時候再看,萬一預賽就被淘汰了呢?備戰了這么久的奧運會,你都不看人家一眼。”這大概是網友最受用的一次“被譴責”。
女子速滑出現頹勢,她很生氣:“干啥!上去就是一頓蹽!管他是誰呢!”中國隊員在接力比賽中意外跌倒,人們的驚訝很快變成了沮喪,而王濛雙手環抱胸前,用親身經歷給所有人打氣:“不用擔心,踢刀會有判罰。裁判現在把規則找出來好好地去看一下。”等到官方判罰結果真的公布出來,王濛興奮得錘桌:“我說什么!”她啪啪地拍著桌面:“我就問,我這教練是白當的嗎!”和前幾次一樣,旁邊的黃健翔只能頗為“弱勢”地感嘆:“有你這句話大家就踏實了。”
中國傳統的體育賽事解說提倡情緒穩定、簡明扼要、敘評得當。黃健翔本是其中異數,但這次遇到“野路子”的王濛,也被襯得“平平無奇”。她能嘮、敢說,在直播間一激動,就不管不顧地離席大喊:“消停的,啊呀呀呀!”“這么脆弱嗎?刮股風就倒了?”她對韓國隊大開“內涵技”,也不失幽默地調侃“土耳其大哥”屢屢搶跑。她有時候像嚴師:“自己踹九圈,整那些膠著的沒用”,有時候又像個“老母親”:“大靖兒啊,滑起來,把膠著留給別人。”
普通人未必能聽明白她說的每一句,但那些大幅度的肢體動作、高起伏的聲音語調,就是讓觀眾覺得痛快、開心、親切。
固然與她一口東北話生動、喜感有關,更因為她為人直爽,少有顧及。她不擅長背誦臺本,念那些深情的、宏大的句子時,每個字都透著僵硬和別扭。嘮嗑才是她的拿手戲。她在比賽間隙回憶如何用臟話和韓國隊賽場外互嗆;慷慨把隊服脫下來送給德國運動員,又嫌棄對方運動服難看;她吐槽某個國家奧運村里只有麥當勞,杜蕾斯倒是處處見,一臉正經地揣測:某某某“回去箱子里塞滿了吧”……都是不太有機會聽到的、運動員另外的側面。
她看起來很跩,但并不跋扈。各種綜藝能看出她的高配合度——無論是在江蘇衛視打扮成旋渦鳴人,還是在黑龍江臺披上粗制濫造的龍袍。即便時至今日,她不想一而再地回憶職業生涯中的陰影,也會笑著對記者娓娓解釋,不是我不想說,我只是不想靠這些博取大家的同情和注意。
她足夠自信,當然也源自頂尖的技術實力,充分接受自己,比如她會糾正別人——我的身材不是胖,而是“壯”。
如今也有新樣式的體育明星,比如海淀榜樣谷愛凌。王濛顯然不是精英體系下培養出的運動冠軍。她沒有中西教育背景,也不像羽生結弦,“把使命當做宿命”。
她的成功經歷、運動生涯都中國本土式的。像過去很多運動員一樣,來自偏僻的小城鎮,被體校發現、選拔,在艱苦的集體生活和訓練里,鍛煉出卓絕的意志。他們把“為國爭光”刻在血液中,在有限的職業生命里,克服傷痛,創造巔峰或失敗,終歸于沉寂。
王濛也走過這樣的軌跡。她的家鄉是黑龍江省七臺河市。這個常住人口60多萬的地級市,遠在“大公雞”的嘴尖上,在奧運會冰雪項目注意力掃過前,它的特產只有煤。很多年后,媒體跟隨著王濛回家鄉,她輕快地回憶:父母起初對職業運動陌生,是啟蒙教練拎著酒上門喝上一頓,才把她帶去了體校。她幼年滑冰摔得滿臉是血,拿袖子蹭蹭接著練,血跡凍住了,還以為是一道一道的鼻涕。她少時睡在體校宿舍,得用兩只手丈量出精準的距離,才能不從上鋪掉下去。
通常她的教練們說起這位徒弟,很難不帶著笑。比如曾任中國短道速滑隊主教練的李琰,認為王濛要是去踢女足,也能進國家隊。她有頂尖運動員特有的聰慧,每塊肌肉都帶著運動的直覺。她是中國短道速滑隊里最愛琢磨器械的運動員,通常其他隊員每天磨刀十來分鐘,王濛要花上一個小時和她的冰刀獨處:磨,校準,琢磨數據。曾經有隊員也想“整器材”,不得其法,向她求教“器材怎么整的,怪不得你滑得這么快呢”。她愛速滑,力求甚解。賽場內,她要搞清楚比賽規則,沒有翻譯,也要抓住國際滑聯技術代表,一幀一幀地看視頻,請教兩個小時。賽場外,她想弄明白為什么荷蘭人滑冰那么在行,就沿著人家境內的一條條河流去“搞調研”。
這位中國短道速滑界的天才,巔峰時期出現在2006-2010年。那些年,王濛出征比賽,拿回來的獎牌、金牌有時多得用袋裝。但她絕非一個金牌機器。除了滑冰,王濛喜歡足球、乒乓球、羽毛球、臺球等一切球類運動,還能賽車,跑馬拉松、玩電競。早年在隊里的聯誼會上,她模仿洛桑學藝,讓隊友印象深刻。她唱歌不錯,相聲說得好到讓人刮目相看——后來她的耳機里,干脆放自己的相聲段子。
當然,她的身上有刺頭的部分。尤其在滿是嚴格的規章、背負沉甸甸任務的體育世界,她的個人意志有時與大環境沖撞得厲害。她的反應可以歸納為——那我走。她大概是極少數,對鏡頭說出“我要回地方隊訓練,因為國家隊訓練不適合我”的悍將。不過這個故事以任性開端,也有很性情的結尾——在一場勝利之后,王濛滑向場邊,對著主教練磕了一個頭,師徒冰釋前嫌。
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王濛奪得女子短道速滑500米冠軍,與恩師李琰緊緊相擁
再后來,王濛退役了,她后來的故事也漸漸少人關注。要不是這次解說意外走紅,人們可能根本不會知道,在職業生涯結束后,王濛也在為人生余下的幾十年,繼續摸索一條并不那么順理成章的路。
短視頻興起后,她成立了一家MCN公司,打定主意要給退役運動員找一條路:“讓社會重新去接納他。為什么(運動員)要直播要帶貨?不然他怎么生活?他也需要生活,需要產出價值。”這家公司沒有社招或是校招,只面向退役下來的運動員。有人適合臺前,就培養做主播;有人適合幕后,那就學習做攝像、做中控。
關鍵詞: 貴圈|如果不是北京冬奧會 你根本不知道王濛退役8年都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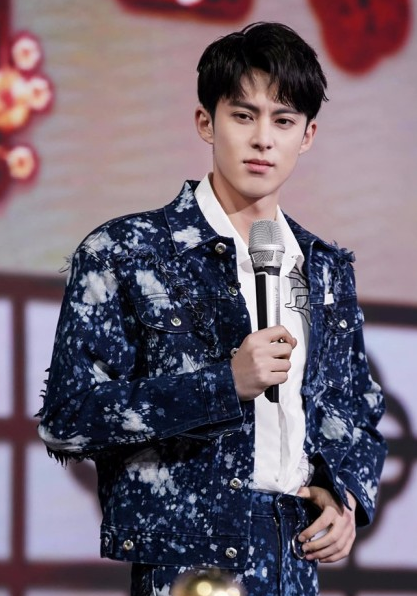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