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人世間》:頓悟“喂不飽”的喬春燕,為何不想看周秉昆東山再起
周秉昆出獄了,他想要買輛小貨車,和“兄弟姐妹”們一起靠搬家賺錢。可是,小貨車要6萬塊,鄭娟這些年節衣縮食,也不過存下了6千塊,實在是杯水車薪。周秉昆便想要找喬春燕借。
喬春燕和曹德寶這幾年做了些小生意,日子過得越來越好,手頭也寬裕了很多。周秉昆張口借,曹德寶本不想拒絕,卻被喬春燕潑了一頭冷水。喬春燕說:“別天真了,自己傾盡所有,幫別人白手起家。”
喬春燕口中的“別人”,是她幾十年來,口口聲聲喊“哥”的---周秉昆。趴在新家的陽臺上,透過落地窗看到周秉昆一行人在搬家賺錢,喬春燕又酸了起來。周秉昆入獄十年,雖然喬春燕嘴上說著“想念”,但這份“想念”過于輕薄。她既沒有幫過鄭娟,也沒有看過周秉昆,反而仗著與周秉昆的友誼,榨干他的社會關系。
說到底,喬春燕始終是喂不飽的“吸血鬼”。
看過《人世間》原著的結局后,我才發現,現實中盡是“喬春燕”這樣的利己主義者,而少有“周秉昆”式的利他之人。
“酸葡萄”
喬春燕是我讀過《人世間》原著后,最討厭的人物。從她死皮賴臉地倒追周秉昆時,我就覺得她是一個“有企圖心”的女人。喬春燕告訴周秉昆,你知道我為啥喜歡你不?因為你和別人不一樣,你有知識、有主見。
周秉昆雖不及哥哥姐姐那般優秀,卻也在他們的熏陶下,比光子片的其他孩子都有思想、有文化。喬春燕處處與人比肩,找對象當然也要找與眾不同的。只是,任憑喬春燕如何撩撥,周秉昆都不為所動。
萬般之下,喬春燕配合母親,夜宿周家。以為生米可以煮成熟飯,卻不曾料想,周秉昆就是個“唐僧”。喬春燕不想再與周秉昆耗時間,便轉移了目標,鎖住了僅有一面之緣的曹德寶。曹德寶是醬油廠的工人,工人的地位總比“修腳工”要高很多,雖然曹德寶沒什么文化,但他會吹口琴,長得也算清秀。說出去,也還算有。
于是,喬春燕就歡歡喜喜地嫁人了。
嫁給曹德寶后,喬春燕很快就為曹家生了個兒子。可是,兩個人卻疏于對兒子的管教。兒子高考那年,因分數太低根本上不了大學。喬春燕很生氣,但更生氣的是,周蓉的女兒馮玥竟考上了清華大學。
喬春燕氣呼呼地說:人家馮玥一個女孩子,都能考上清華。我這兒子怎么連個大學都上不了。周楠獲得國外大學的獎學金,出國留學時,喬春燕更是嫉妒得跳腳,直到聽說周楠在國外遇害,才面色緩和了下來。
以前聽人說過,最喜歡和你比較的人,往往是你的親戚朋友。因為他們在你的生活圈,因為他們需要在你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優越感。
清華大學、國外留學,何止周楠一個?但喬春燕不認識,她只認識周楠和馮玥,也只能和他們比較。其實,這樣的事,我們生活中也常常遇到。
上學時,周圍的親戚朋友見了面,會問你成績。如果你的成績好,沒有人會真的為你開心,而如果你的成績不好,他們便找到了優越感,也打開了話匣子;長大后,周圍的親戚朋友見了面,會問你在哪高就。如果你足夠平庸,他們會笑話你沒出息、如果你還不錯,他們也不會真心認同你,反倒會找出自家孩子的長處,狠狠地把你比下去。
總之,人與人之間就是喜歡比較。“酸葡萄心理”使得大部分人,不會真心為他人的成就而高興。也正因如此,現實中像“周秉昆”這樣的人,才會顯得難得。因為他從來都不嫉妒別人過得比他好,只一步一個腳印地過好自己的日子。
周秉昆的哥哥姐姐考上大學時,他還只是個每月拿著18塊工錢的工人。后來,哥哥姐姐分別成了干部和教授,周秉昆依然是個“平頭百姓”,父母明顯高看哥哥姐姐,周秉昆難過,也絲毫沒有生半點嫉妒之心,只是努力過好自己的日子,讓父母對他刮目相看。
喬春燕當上婦聯副主任,得到寬敞的大子時,周秉昆從來都是為她高興,然后默默攢錢,想著給自家換間大子,從未話里話外地酸過一句。
在周秉昆的心里,別人的成功都是別人的。自己不羨慕也不嫉妒,因為與其那樣,還不如打好自己手里的牌,過好自己的小日子,才算對得起家人、對得起自己。
虛偽的“真心”
都說,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通過互相麻煩,才變得親密的。但我是一個不喜歡給別人添麻煩的人,也覺得麻煩別人也要有底線。最那些拿著“麻煩別人”不當事,別人不幫忙就死纏爛打鬧情緒的人。
在《人世間》中,喬春燕就是這種人。
結婚幾年后,曹德寶因為喬春燕的精明,而疏遠于她。喬春燕擔心會離婚,哭鬧著跑去周秉昆的飯店,不管不顧地質問曹德寶,是不是外面有人了。飯店要做生意,喬春燕那般歇斯底里地喊鬧,會造成很大的影響,但是喬春燕卻滿不在乎。
因為她只顧自己,不顧別人。末了,還警告周秉昆,“我和曹德寶的事,你必須得管,因為我們倆是你給撮合成的。”喬春燕和曹德寶是怎么在一起的?她自己比誰都知道。何況,人家周秉昆即便是介紹人,哪怕家庭不睦,也和介紹人沒關系吧?讓人家負責,還說得那般理直氣壯,就確實有些過分了。
事實上,喬春燕找人幫忙,一向那么理直氣壯。曹德寶下崗后,喬春燕找周秉昆,托周秉義安排搬家的事。周秉昆拒絕了,卻幫了差點因為被騙而入獄的孫趕超。喬春燕火了,她沖到周秉昆的飯館,質問他為什么不肯幫忙,并口口聲聲說要“絕交”。
周秉昆一向是能幫就幫,但他也不愿意事事麻煩周秉義。畢竟,周秉義為人公正,也有很多自己的為難之處。況且,在周秉昆看來,喬春燕的求助,只不過是吃不上“肉”罷了。算不得“吃不上飯”的大事。
我總覺得,朋友之間的關系有兩種。一種是相互取暖的純朋友,一種是利益置換的好朋友。對喬春燕來說,周秉昆顯然是屬于第二種,因為她不需要“取暖”的朋友,只想要從朋友身上榨干價值。
但“利益置換”,也要發生置換。喬春燕有求于人時,周秉昆家沒少出力,包括喬春燕的兒子離家出走、她因被總經理坑騙而入獄,周秉義都沒少幫忙。但是,輪到周秉昆張口尋她幫忙時,喬春燕卻露出了精明的一面,各種理由推不說,還別人日子過得紅火。
見到周聰在報社當記者,周秉昆出獄后也很快有了工作,喬春燕的心便又失衡了。她故意在馬路上喊:“父子雙雙把班上啊,這周家祖墳上算是積了大德了。有市委書記這么硬的后臺,那誰怕啊?絕對的享福。”
馬路上都是人,喬春燕就是要讓所有人都聽到。好像周秉義這個干部真的在背后幫了多少忙似的。當初,喬春燕沒有借周秉昆買車的錢,也是看準了周秉義不會回到吉春當領導。既然無利可圖,又何須顧忌朋友?后來,周秉義回來了,還組織了光子片的拆遷活動。
喬春燕心里著急,生怕周秉昆不幫忙,便又巴結上了他。
說到底,朋友對喬春燕而言,就是為自己服務的“工具”。她這樣只顧自己得意,不顧朋友失意的人在現實中很多。你可以認為,他們是窮怕了,但我卻覺得,一個人做任何事,都是出于自己的選擇。既然沒有真心,又何故口口聲聲地稱兄道弟?
或許,我的想法過于“方鴻漸”了,但凡事只談利益,終日以面具示人,真的好嗎?反觀周秉昆,他幫助別人,從來不圖回報,也不圖他人的社會地位。能幫,周秉昆一定會幫;想交的朋友,也一定真心相待。
這樣的人,難道不溫暖嗎?
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喬春燕聽說周秉義要組織光子片拆遷、分,便打起了如意算盤。原著中,喬春燕因為不滿周秉義的分,一封匿名信告到了上面,非說周秉義不公正,并拿了老百姓的錢。
雖然周秉義是清白的,卻也因為調查而延誤了病情。最后,因為病情沒有得到控制,而離世。電視劇中,喬春燕是一定會在子的問題上“作妖”的。為了能多算一些面積,她拉著曹德寶,緊鑼密鼓地在院里蓋起了小屋。喬春燕告訴喬母,自己想多爭取一間,好分給兒子牛牛。
能理解父母為兒女打算,但人人都像喬春燕這般,工作就很難推進了。畢竟,眾口難調,不可能讓每個人都在應得的基礎上,再額外沾到便宜。可是,喬春燕才不管這些,她只想著自己。
羅馬首位喜劇作家普勞圖斯曾說:“人人都是自私的。”
我能理解喬春燕的自私,卻無法茍同她的自私。正如成功的能接受別的女人說獨立,卻不允許自己子放棄家庭,外出工作一樣,我不認為“自私”地與人相處,是生而為人唯一的選擇。
周秉昆當初沒工作,也需要錢,卻依然因為鄭娟,而拒絕了5元的跑腿費;周秉昆家里住困難,全家6口擠在兩個間里,卻依然二話不說,幫周蓉撫養馮玥;自己的事不敢求周秉義幫忙,為了朋友卻一再麻煩周秉義。
當然,像喬春燕這樣的“朋友”,也確實不該交、也不該幫,但周秉昆貴在有一顆赤誠之心,從來都是能幫則幫。
喬春燕“利己”,周秉昆“利他”。人人都笑周秉昆“癡”,為了幫助別人,不惜得罪別人;為了保護想要保護的人,不惜傷害到自己。人人都稱喬春燕才是“人間清醒”,活得現實。
但我卻不以為然。
正如列夫·托爾斯泰所說:“這是個充滿掠奪、自私自利的世界。所以,少數表現得不自私,愿意幫助別人的人,便能得到極大的益處。”
關鍵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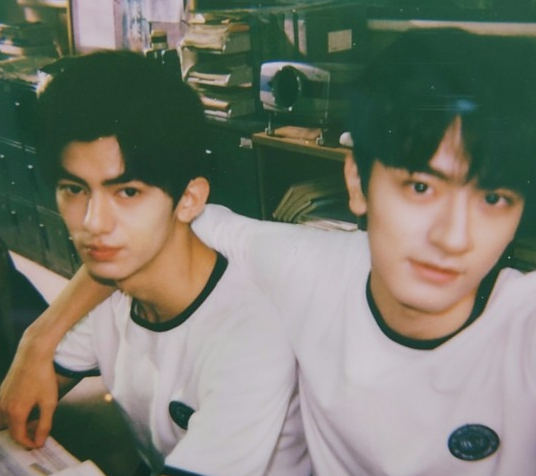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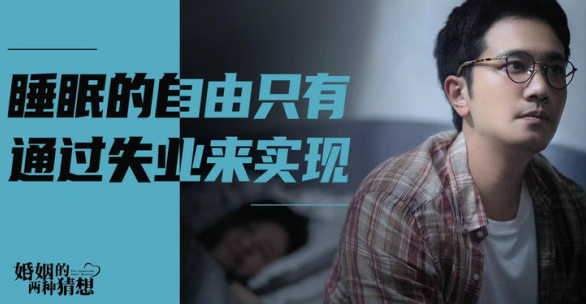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