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結束的第72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上,導演卡拉·西蒙的第二部長片《阿爾卡拉斯》擒下了金熊獎,完成了自去年戛納開始的女性導演最高獎項三連冠的壯舉。
而老牌女性電影人克萊爾·德尼以及柏林常客洪常秀也分別憑借《雙刃劍》與《家的電影》拿下了最佳導演與評審團大獎。
值得一提的是,李睿珺導演的《隱入塵》雖然沒有斬獲,但此次入圍主競賽單元也是終結了2021年度華語電影同時缺席歐洲三大的境況。
當然,本屆角逐金熊獎的18部影片內,由弗朗索瓦·歐容執導的新作《彼得·馮·康德》原是最高獎的有力競爭者,但這部翻拍自法斯賓德名作《柏蒂娜的苦淚》的開幕片,卻并未受到評委以及觀眾的青睞。
近年來,不知是因為屢屢被三大拒之門外,還是年歲漸長帶來的創作熱情褪去,歐容的作品逐漸開始呈現出對貫徹作者性的力不從心。
2016年的《弗蘭茲》一改先前奇情先鋒的影像表達,轉而用上含蓄內斂的語調敘述了一段戰后愛情故事,延續這一風格的《感謝上帝》則是用更加客觀與抽離的手法還原了神父孌童這一現實題材。
有趣的是,這兩部變換了風格的影片反倒比歐容回歸原初的創作收獲了更多好評。
因此,去年入圍戛納主競賽的《一切順利》,更像是歐容對當下市場審美的妥協,但在融合了《弗蘭茲》的沉著與《感謝上帝》的現實性之后,卸下了奇技淫巧的成品卻意外有些水土不服。
這部影片改編自與歐容有過多次合作的編劇艾曼紐·貝爾南的同名,講述了一段女兒幫助父親安樂死的故事。
熟悉歐容的觀眾似乎光是看這個簡介便能會心一笑,死亡已經是歐容相當迷戀的一個作品元素,在其前作《85年盛夏》里,更是出現了“墳頭蹦迪”這般令人瞠目結舌的橋段。
但在《一切順利》中,先是死亡的含義被局限在了肉體消亡所帶來的解之中,爾后針對安樂死這一話題性十足的完成死亡儀式,歐容都沒能帶上任何的思辨與深度探討,反而是在一種結果導向的創作思維里陷入了平鋪直敘的陷阱。
所以整部影片就無可挽回地降格為八點檔的家族群像戲與如何安樂死的指南手冊,這一點,相較于前中期的歐容來說,幾乎是表達上的斷崖式下滑。
尤其是當我們知道艾曼紐曾經與歐容拍出了《泳池情殺案》以后,這份落差會顯得更大,因為那些人物的刻畫、故事的張力與影像的拿捏,全部消失了。
就拿蘇菲·瑪索飾演的艾曼紐來說,導演早在影片的前三十分鐘內,就已經利用一塊三明治的軌跡完成了觀眾對于她的心理預期建設。
于是,這個人物的神秘感一下就被消解了,當三明治被扔進垃圾桶的那一刻就預示著女兒助推父親安樂死的必然。所以我們不會再去于她最后做出的抉擇,而是更想窺探選擇背后的心理因素。
但這個本該是全片最深刻的情緒轉換,被歐容以一種輕描淡寫的方式拐了過去。我無意將其看作是歐容導演技法上的舉重若輕,反而更覺得是他在處理上的保守與避重就輕。
因為光是憑借 幾處點到為止的回憶與夢境,以及一段并不高明的關于女兒與朋友身份轉變的對話,尚不足以喚起我的理解與共情。
如若是同《感謝上帝》那般將情感完全沉淀,那么這塊沉積的洼地又落在了影片中的何方?歐容沒有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承載物,而在蘇菲·瑪索從頭至尾隱忍克制的表演下,二者是無法自圓其說的。
又或者,當我們擴大到父女間的關聯,那勢必又帶來另一番家庭維度的探討。然而這個表面上看起來的家庭群像,其本質卻是落在了由安德烈·杜索里埃飾演的父親身上那根深蒂固的精英主義。
影片對這份精英主義做了相當詳盡的刻畫,例如流露在窮人都無法選擇安樂死上的優越感,對鄰床病友的回擊所展現的階級自覺,甚至于把女兒調侃是“兒子”的家長式趣味。
凡此種種,無不是將安樂死的選擇簡化成為父親對疾病纏身的自己無法維持上層階級的體面所尋求的主動解。如此乏善可陳的內在驅動等于是主動屏蔽了父女間本該擦出的的情感火花,同時也讓父親請求女兒助他死亡的震撼力下降不少。
更不必說,母親,同性愛人,乃至姐姐帕斯卡爾都淪落成整個故事的背景板,他們串聯起來的情感網絡幾乎都是服務于父親一人,貧瘠的互動使得拼湊出父親完整形象的最后一絲可能也消失殆盡。
而這些,本該是這部作品最為基礎的底色,在這之上,才能衍生出關于安樂死道德困境與法律邊界的更深入描繪。不過,在根基尚未牢靠的前提下,歐容倒也沒有貿然地把后兩者囊括在這部電影的議題內,更準確地說,歐容反其道而行之地為我們展示了突破法律邊界,順利安樂死的方法。
這是影片后半程敘事上一個很大的問題,從“要不要”安樂死變成了“如何申請”安樂死,等于是犧牲了本該有的故事張力轉而走向了更為穩妥卻無趣的糖水片范疇。
哪怕影片的視點是一次相當私人化的選擇,但如此直白且毫無回響的敘事理應不該出現在歐容的作品序列中。
尤其是最后階段警方的突然介入,更是給我一種劇情編排上的算計之感。把先前提到的萊奧奈蒂法與交給公證人的視頻當作“契訶夫之”,目的自然是為了照應安樂死本身在法律上的模棱兩可。
但這一點小小的起伏也很快淹沒在一切順利的話語中,變得拖沓且毫無必要。
而在結尾處,歐容省略掉父親安樂死的整個過程,只余下蘇黎世女士和兩位女兒通電話的鏡頭,無疑是丟棄了整部影片最核心的靈魂,再次讓父親與女兒各自的形象塑造大打折扣。
作為觀眾,我會更在意父親面對死亡真正的到來所做出的反應,以及借由整個安樂死的過程側面印證出的作者態度與傾向性。
但這些都沒有,只剩下最后一幕蘇菲·瑪索那眼淚含混著笑容的面龐。
是喜還是悲已不再重要,停留在淺層次情感上的挖掘并不會引導出多義性的結論。
說了這么多,回過頭來看的話,或許歐容這般自我休克式麻痹的打算,早已反映在“一切順利”這個片名內。放棄了一切節外生枝,也讓影片毫不意外地滑向了平庸的境地。
其實按照目前歐容風格化與反風格化作品交替出現的軌跡來推測,他似乎依然搖擺在市場與自我表達的天平兩側。
我們或許難以等到下一部《登堂入室》,但我們依然期待著尋找到平衡點后的那個更加成熟的歐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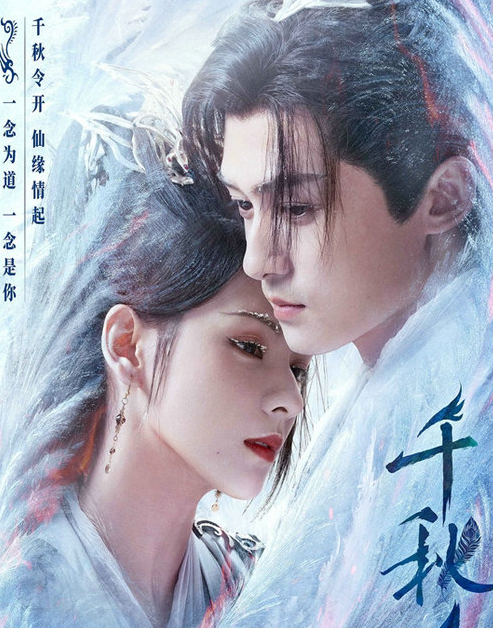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