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十點電影原創
暗巷里兩聲槍響,珍珠項鏈灑落。
一個男孩在痛苦和血泊中,絕望呼喊。
二十年后,一個神秘如吸血鬼的人物,駐守于墮落黑暗的城市中。
他是超級英雄史上,最有名的人類英雄。
蝙蝠俠。
如今頂著全球疫情的壓力,他,再次逆風上線。
《新蝙蝠俠》的主演羅伯特 ·帕丁森,在影片開拍之前,曾有一句出名的宣言:
“如果《新蝙蝠俠》的票房慘敗,我就去下海。”
雖然確實是玩笑話,也不難看出。
在漫威風光已過,超級英雄題材已經不在新鮮的當下。
想再一次為“蝙蝠俠”這一名字賦予榮光,該有多難。
更何況,蝙蝠俠的電影,早有成功案例在先。
諾蘭的《黑暗騎士》系列,早在近20年前,大獲成功,成為影史杰作。
后來的本·阿弗萊克飾演的蝙蝠俠,口碑好壞參半。
由他執導的蝙蝠俠系列也因此擱淺。
改換《新蝙蝠俠》導演馬特·里夫斯執導。
曾主演《哈利波特與火焰杯》《暮光之城》的吸血鬼男主角,羅伯特·帕丁森接棒。
英文片名的《The Batman》也明示:
它不再是諾蘭經典的翻拍復刻,他將重回歷史性的源頭。
“世界第一偵探”,和他的黑暗家鄉,“人杰地靈”邪惡之城,哥譚。
這很難不讓人想起蝙蝠俠的那句經典臺詞:
"I am vengeance. I am the night. "
"I am Batman!"
不得不感謝電影,沒有從最經典的犯罪巷故事講起。
不再重復老套的起源: “每拍攝一部蝙蝠俠,就有一對韋恩夫婦被殺害”。
《新蝙蝠俠》的故事,直接從布魯斯韋恩當上蝙蝠俠的第二年開始。
快兩年的時間,蝙蝠俠已經樹立起了自己的名聲:
恐懼,復仇,“我就是陰影。”
但這一切并未將哥譚指向光明,反而哥譚在黑暗中越墮越深。
蝙蝠燈打亮的夜晚,大雨傾盆,街道卻是沸騰。
光和聲,不是夜生活的繁忙。
而是商店玻璃破碎的打砸、毒販子和小混混聚集的篝火。
但所有人都會時不時望向黢黑的通道、潛藏著陰影的角落。
恐懼已經在每個人的心中建立:蝙蝠可能隨時降落在你頭上。
這也不是蝙蝠俠第一次面對腐壞暗黑的哥譚。
導演提及,電影的改編來源有《蝙蝠俠:元年》《蝙蝠俠:漫長的萬圣節》。
最突出的一本是《蝙蝠俠:自我》,講述蝙蝠俠重新認識自我的故事。
也正如在《蝙蝠俠:地球一號》里的年輕版布魯斯一樣。
《新蝙蝠俠》里的布魯斯,內心充斥著為父母復仇的怒火。
主演曾在采訪里提過:布魯斯每次打擊犯罪,都把那些罪犯視為殺害他父母的兇手。
甚至,連被他救下的受害者,也會瑟瑟發抖,請求他放過自己。
他唯一的朋友,警長詹姆斯戈登。
當他行走在警局里時,每個人都以異類的眼光看待他。
但他非來不可。
此時,哥譚的政治大佬、警察局長,正一個個被殺害。
兇手謎語人留下一個又一個謎題,誘偵探深入。
賀卡、密碼,還有謎語人的標志性簽名:一個問號。
跟隨著每一個線索,蝙蝠俠對哥譚的了解隨之加深。
他看到,號稱已經被清掃的販毒利益網,竟然被哥譚警方染指。
黑幫大佬和警方高層,在地下俱樂部狂飲,涉黑警察,在為毒販頭目兼職看門。
甚至,黑暗,越來越向著孤獨的韋恩大宅靠攏。
明面上,深居簡出的富豪布魯斯收到了炸彈,親近之人受傷。
暗地里,早已廢棄的孤兒院,藏著韋恩家族不光彩的過去……
顯然,編劇在這里又藏著致敬漫畫的彩蛋。
正如漫畫《地球一號》一樣,布魯斯的母親出身阿卡姆家族,血脈里暗藏著瘋狂。
而布魯斯韋恩的父親,也在多部漫畫中和反派法爾科內打過交道。
沒有媲美外星文明的高科技,沒有全明星陣容的正義聯盟和蝙蝠家族的支撐。
蝙蝠俠唯一要面對的,是他的敵人,謎語人。
或者說是同類,更為恰當。
同樣是孤兒出身,一個被金錢包圍,一個被貧困裹挾。
窮和富,兩面一體,正與惡,歧路殊途。
片中也有其他反派。
像科林法瑞爾飾演的企鵝人,戰斗力被猛削,險些淪為搞笑角色。
再像哥譚幕后黑手法爾科內,唇齒鼓動人心,鏡頭寥寥可數。
而謎語人試圖復仇的對象,其實并不是他們。
是哥譚,是這座城市,是這座城市里的墮落者。
他只希望他的模仿對象,蝙蝠俠,與他共同觀賞這場大戲。
哥譚永遠在腐朽,徹底毀滅才是唯一的出路。
而蝙蝠俠在哥譚的夜晚中,也碰見了另一位“怪胎”。
“貓女”賽琳娜。
平時打扮性感,在俱樂部里打工。
到了夜晚,則換上另一套裝扮,翻窗溜鎖,直奔犯罪現場——
她有她的路要走。
和蝙蝠俠的緣分,注定只是黑夜里的偶遇。
《蝙蝠俠》中的每一個片段本身就是一個事件。
四處充溢著緊張的能量和令人不安的氣氛。
導演一點沒放棄自己對傳統“黑色電影”的致敬。
仔細看就能發現,哥譚市的政治風云、街頭景象。
和《唐人街》《總統班底》里的洛杉磯華盛頓如出一轍。
他還為《新蝙蝠俠》帶來了最“經典重現”的效果:
看它,就像是看一本印刷在粗糙紙上的漫畫書。
顆粒狀紋理、弱光、模糊背景細節的淺景深效果。
對于蝙蝠俠來說,最大的挑戰,不是反派,而是黑暗。
無論是字面還是隱喻,黑暗都在將蝙蝠俠和哥譚市的所有人,一起吞沒。
但攝影師格雷格·弗萊瑟沒有讓整部電影完全沉迷于黑黢黢的氛圍當中。
這位掌鏡過《沙丘》、《曼達洛人》的幕后大咖,一直確保每個鏡頭中都有光亮的部分。
在被黑暗包圍時,光明仍未休止。
配樂同樣可圈可點。
當那段蝙蝠俠專屬配樂響起來時,極具壓迫感的陰暗,在耳邊凝聚成實體。
如果你仔細聽,還能聽見金屬感的腳步聲。
這像什么?
像是西部片,沒有馬刺的牛仔,也像是沒拿槍的孤單英雄。
這正是蝙蝠俠為自己劃下的底線。
拒絕槍械,不殺原則。
所以你能看見他出拳險些將兇犯打死,也能看見他搶過槍支當撬棍用。
這是蝙蝠俠永恒的不同。
泛濫熒幕的超英片里,正派不是超能力加身,就是天生神力,高科技加成。
聰明、有錢,集時髦拉風于一身。
反派不是在傻氣和嫉妒之間游走,就是最后笑點加身,淪為喜劇角色。
而蝙蝠俠,從來都是最接近黑白界限的那一個。
哪怕對親密隊友也留有“后備計劃”。
在電影中,他在現實的危險邊緣游走,瀕臨憤怒失控的高壓線。
堪比《速激》的追逐戲里,汽車金屬燒到嘎吱作響,輪胎尖銳摩擦。
導演把觀眾也綁在了引擎上,讓所有人一起體會車隨時可能解體的壓力。
沒了厚重的護甲,他也面臨著更直接的傷害。
步槍懟臉轟擊、棒球棍和砍刀,連一場爆炸,都可能讓他直接陷入腦震蕩昏迷。
甚至,還有堪稱黑歷史的“新手時刻”。
第一次被逼上天臺,第一次用上滑翔翼。
你以為是超酷炫的凌空飛翔?
跳躍部分整挺好,至于落地嘛,連撞立交橋再撞公交車。
多少是有點尷尬了。
但對于他,對于一個以凡人之軀比肩神明的神話來說。
在今時今日,又那么恰到好處。
“出道即巔峰”只是傳說,無人可以直接攀爬到頂峰。
本文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聯系刪除
用不著再解釋,為什么不選擇殺戮,為什么復仇不是最好的方式。
為什么哥譚如此混亂,卻始終不離不棄。
他在學習,我們也是。
而和菲尼克斯版《小丑》互相輝映,《新蝙蝠俠》也在重新書寫一種新的英雄敘事。
世界的復雜和混亂正在與日俱增,英雄和反派不再是唯二焦點。
再也沒有永恒不落的明星,有的只是隨著流量浮現的獨行者。
我們都在適應這個時代。
我們都在混亂中試圖抓住機會,在黑暗中尋找方向。
“誰說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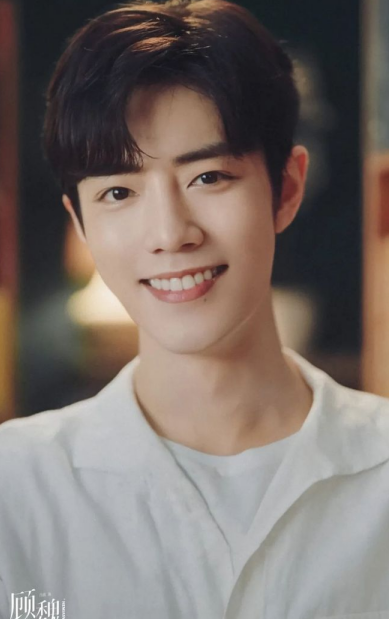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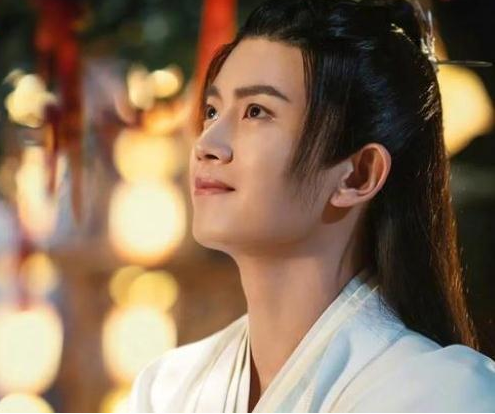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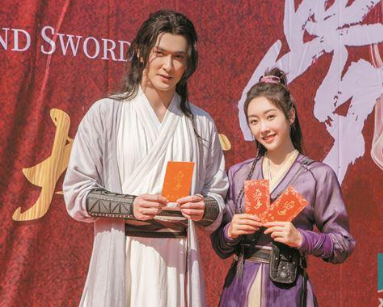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