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小橙子妹妹
《我的姐姐》一經發布,好評如潮。然而,高票房的背后,又有多少“姐妹”在流淚。
張子楓作為童星出道,第一次扮演女主人。在他極具感染力的演技背后,我看到的是“妹子”二字,給生活帶來了無法承受的重量。
一場車禍帶走了我的爸爸媽媽,留下了一個還在上幼兒園的弟弟。弟弟是在妹妹上大學后來到這個世界的。可以說姐姐和弟弟幾乎沒說過幾句話,更談不上有過什么感情。
因為這次意外,弟弟的撫養權成了最大的問題。
在親戚們的一致討論下,妹妹無疑成了弟弟最天然的監護人,但這些親戚們都忘了,妹妹才20出頭,剛大學畢業,連自己的生活都需要吃緊。
她“恨”弟弟,這種“恨”不是沒有原因的。
為了拿到生二胎的許可證,也為了弟弟的出生,姐姐不得不裝成“瘸子”。
明明大學能考得好,能改變自己,父母卻偷偷篡改姐姐的意愿,選擇當地的學校,只是為了更好的照顧弟弟。
上大學后,妹妹賺足了所有的開銷,而弟弟每天早上都能吃到熱騰騰的肉包子,妹妹二十多年來從沒吃過父親做的紅燒肉。
但凡姐弟倆有一點爭執,妥協的那一方永遠是姐姐。
但凡有一個人要犧牲,毫無疑問,那個人必然是姐姐。
在電影中,我姐姐的姑姑說:“我是姐姐,從生下來那天就死,一直都是。”總是在想,為什么我姑姑要強調這句話?
后來仔細想想,才知道阿姨的話里有很多無奈。在我姑姑的時代,我家不可能只有一個女孩。她知道她會有一個弟弟。
大部分姐姐一出生就被打上“姐姐”的烙印,所以她一輩子都想隨心所欲做事的可能性非常小。
舊時代的“黃歷”中,“姐姐”這個群體似乎自出生起,就背負著“妥協”和“犧牲”的標簽,女性在“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下,做著加法,而“姐姐”的故事在代際遺傳中,依然延續著。
列夫托爾斯泰曾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起初不太明白,但后來他仔細了解后才知道真相。
我們姐妹的故事都大同小異,看著發生在“姐姐”身上的故事就忍不住淚流滿面。
雖然不是故事中的主角,但主角的故事真的發生在他身上。
姐妹們經常反思:“是我不夠好嗎?是我的錯嗎?所以父母一定還有一個哥哥?”
其實我姐沒什么問題。在一個中國家庭里,當“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的遮羞布被撕掉,姐姐有什么不好?
我還記得,在《奇葩說》的一期里,傅首爾談到二胎的話題時,給我舉了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例子。
她說:“當一個
孩子手里有一百顆糖,他怎么會介意分享,當他手里只有兩顆糖,你又憑什么要求他大方。”連小孩子都知道的道理,大人卻時常犯迷糊。
當孩子感受到愛的失衡,其實,在那一刻,她的心里就已經埋下了一顆種子,不安、不自信,以及自我懷疑,而這些將會伴隨著她們一生,或多或少。
曾在某乎熱評中,看到這樣一句話。
“我的父母好像會選擇性失明,選擇性看不見我。”
獲贊無數的一句話,卻讓我淚目。
想要逃離原生家庭的束縛,卻被血濃于水的親情所羈絆,姐姐們的逃離之路,似乎永遠走不到盡頭。
費孝通曾在《鄉土中國》說:“西方的家庭關系就像一捆木柴,雖然被家庭的紐帶綁在一起,但是作為木柴個體而言,他們還是獨立的,彼此之間的界限是明晰的;相反,中國人的家庭關系更像石子投到水面后水面上的漣漪,是一種由己推人的模式,你很難分清楚彼此之間的界限。”
這大概就是中國式家庭更難以理清親情的原因了,而姐姐們只能將這種“委屈”埋在心底最深處。
影片結尾處:姐姐放棄將弟弟送養,同時,也意味著她主動承擔起照顧弟弟的義務,不難想到,這是一個大眾普遍都能能接受的結局,姐姐最終還是“妥協”了。
姐姐的“妥協”,卻也讓我們看到了姐姐在掙扎中的最后選擇,而此時,姐姐的“妥協”不是犧牲,而是甘愿!
這大概就是影片最想要告訴我們的,愿父母愛的天平,不再失衡,“姐姐”同樣也需要一個溫暖的懷抱。
——完——
(圖片來源于網絡,侵刪)
聲明:原創不易,禁止抄襲、洗稿,未經允許禁止轉載。
關鍵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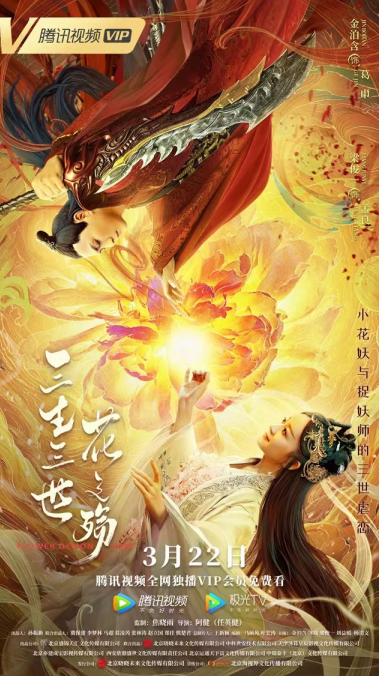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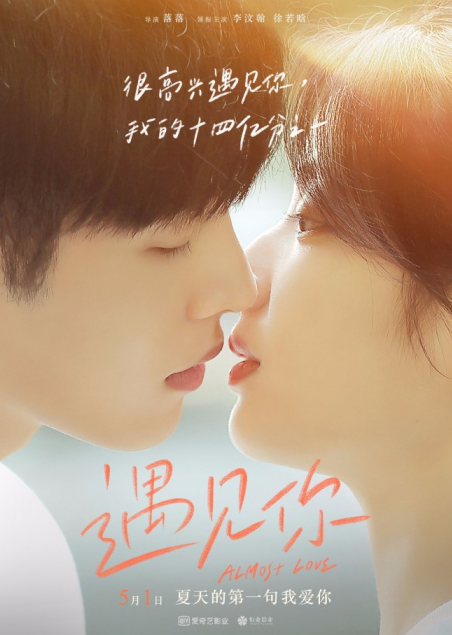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