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斯向前行》是一部紀錄片類型的電影,這部紀錄片的結構簡單,導演在一間大的房間懸掛了許多人物圖片,這些人物全與文德斯有關。
文德斯漫步在圖片世界中,有時駐足評點,有時端詳無語,靜靜沉思。故事由此切入,文德斯的喃喃自語,與文德斯有關的10多位人物的娓娓而談,構成了文德斯的工作、友情、愛情的數個片斷。
傳奇導演的童年
文德斯是焦慮時代的導演。影片開場,他行走在鄉間田野的畫面配有一段深沉的內心獨白:“你應該怎樣生活?我們怎樣才能發現生活的真諦?我們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一旁陪著他的妻子多娜塔說,文德斯喜歡被遺棄的空曠的城市,同時他也喜歡城市,他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
文德斯出生在德國杜塞爾多夫市,他出生的1945年8月,恰好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美國派兵進駐德國,這樣,美國文化也悄然進入了戰敗國。
這樣的環境影響了文德斯的少年生活。他的父親是個外科醫生,不愛說話,在家有絕對的權威,母親性格順從,但管教孩子嚴厲。
文德斯說:“我們兄弟繼承了父親不愛說話的性格。”像昆汀·塔倫蒂諾、斯皮爾伯格一樣,很小的時候,文德斯就接受了影像的啟蒙。父親喜愛卓別林,買了一部8毫米攝影機。
與電影一起長大
12歲時,文德斯用它拍攝了樓下的街道與行人。影片讓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父母的模樣,他家里的第一臺車,家中生活的場景。
中學畢業后,文德斯開始想做個神父,之后還想做個外科大夫。后來,他選擇了學習繪畫,到西方文化之都一巴黎美術學院學習。懷舊的音樂,古老的街道,行走的人群,形影孤單的年輕文德斯來到巴黎求學,他拼命讀書、畫畫。
最后,他發現自己討厭人體素描,甚至覺得“一個人站在我面前讓我畫太荒謬了”。當時巴黎電影新浪潮運動正處在鼎盛時期,文德斯每天一個人去看電影,從早到晚地看,有時一天能看五六部電影,就這樣,他看了上千部電影。
文德斯迷上了戈達爾、特呂弗的電影,他決心學電影并且要拍電影。他離開法國,回到德國慕尼黑電視電影學院繼續學習,成了第一批學習電影的學生。他自費拍攝了3部短片,并撰寫了大量的影評。
文德斯為什么迷上了電影?臺灣萬象圖書公司出版的《文德斯論電影》收錄了他23歲后撰寫的部分文章,其中《你為什么要拍電影》一文,回答了這個話題。
他太愛電影了,起先雖然立志當畫家,大部分時間卻泡在電影院,剛開始只因為一塊法郎可以讓他享受兩個小時的暖氣,但很快上癮了。
“巴拉茲·貝拉說,攝影機能懷救事物的存在深深影響著他。這個世界外貌的逐漸毀滅就這樣煞住了。攝影機是抵抗事物(毀滅)悲劇的武器。為什么要拍電影?這可真是個無情又愚蠢的問題!”
文德斯說,文字是黑暗影院中客觀銀幕的影像與最主觀的銀幕影像與心靈之間的橋梁。除了用我們的眼睛去看之外,電影是不存在的。事實上,電影一向被“看”兩次,一次是編劇、導演、攝影師、演員等,第二次是每一位觀眾。
紀錄片的核心—文德斯的愛情故事
文德斯的愛情經歷,是紀錄片《文德斯向前行》的重要內容,這也許象征了他獨特氣質的另一面。影片中出現的分別是初戀女友尤瑞克,后幾任妻子愛達、利薩、多娜塔。
四個與文德斯有關的女性,面對鏡頭,講述在與他生活的歲月里,文德斯對電影的癡迷、不善溝通的個性。文德斯與尤瑞克的初戀,注定對他的打擊最大,或許是他孤獨之旅的起點。
17歲的文德斯與14歲的尤瑞克初戀了,他們一起滑雪。文德斯沉浸于初戀,認為“那就是永遠”,與尤瑞克一起分享著心目中的偶像加繆、薩特。
文德斯第一次遠行,倆人去了巴黎。文德斯回到慕尼黑學習電影,尤瑞克向他攤牌,愛上了別人,這個人恰恰是他的朋友,文德斯極度震驚,結束了初戀。
孤獨的漂泊者
其實,文德斯的內心世界遠不止“孤獨”兩字簡單,還有空虛、消沉、厭倦、矛盾和死亡。面對鏡頭的文德斯表情木訥,幾乎沒有笑容,話語不多,每一句話都是深思熟慮后的流淌,且富有哲理。他說人生“必須通過一個罪惡的荒野,才能到達天堂”。
現在的文德斯除了拍電影,還寫作、攝影、畫畫,他的攝影作品同樣滿地蒼涼滄桑,妻子多娜塔細心照料他的生活。
她反倒欣賞文德斯孤獨氣質下的沉靜:“我經常告訴他一些事情,他沒有回應,我認為他沒在聽我說,但一兩天之后,他經常說一些很精辟的話,這證明他聽得仔細而且深思熟慮。我們溝通有些時間間隔。那是他的工作方式,他基本上算是孤獨癥患者。”
結語
紀錄片《文德斯向前行》用了一個特殊的結尾方式,文德斯談文德斯,在他與妻子滑冰的鏡頭中,輕柔的歌聲漸起,響起他的同期聲。
人群是一個幻覺,真正可以與智者對話者寥寥。其實孤獨的何止文德斯一個,每個人都是孤獨的,與智者同道,維姆·文德斯并不孤獨,他是可愛的天才,杰出的電影大師。
【免責聲明】如涉及作品內容、版權和其它問題,請在30日內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在第一時間刪除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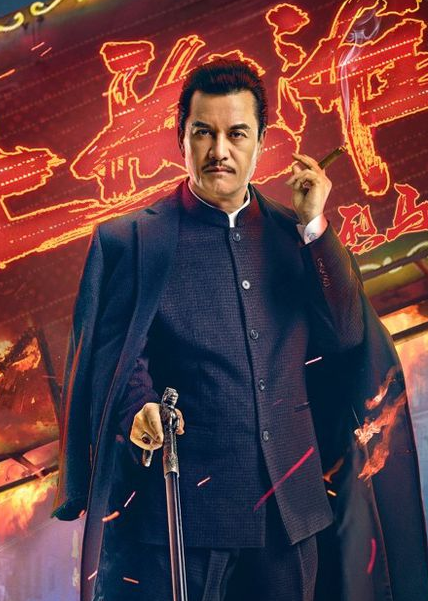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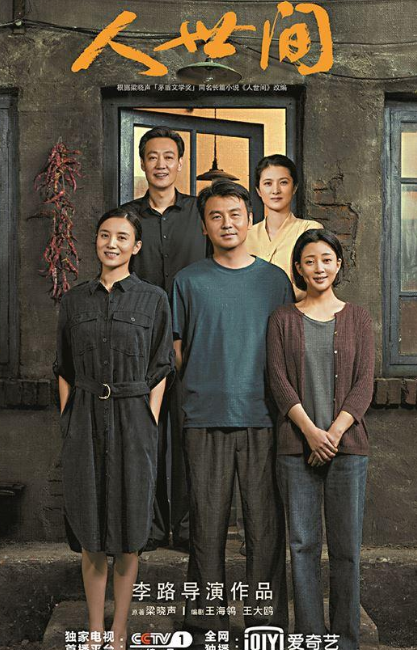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