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遷:2008年,我考學第二次落榜,去了家鄉的一所專科學校,在里面待了四個月,課程很水,宿舍也不裝網絡,每天我就去網吧通宵看電影,基耶的《十誡》是兩個通宵看完的,每天看五個,再一天看《紅白藍》,那陣子是一直看電影,因為郊區確實如小說所寫,一片荒蕪。網吧是學校經營的,晚上9點開始通宵,下午起床后我去隔壁打打牌,有時在自己宿舍里打打牌。然后是2014年,我直到畢業都不能不受限制地拍電影,想著考了這么多年學圖什么呢,就重操舊業開始寫小說,最開始是《大裂》。
新報:你想用這樣的文字表現什么?
胡遷:因為我念過這兩個大學,一個屬于全國墊底的學校,一個算是好學校,而這個所謂墊底的學校,我查過資料,中國百分之七八十都是這種大學,電影學院狀況要好很多。但我覺得這個時代的青年,痛苦的地方都差不多,也就是說環境、家庭、周圍是什么人,都改變不了他們本質上的無所適從,當然有些活得太輕松的人另當別論。我寫《大裂》,也許是為了讓自己記住那段日子,混亂不堪,但有其野蠻的生命力。
這個小說沒什么特別的,我只想真實地描述出中國百分之七八十的大學生過的日子和面臨的狀況。如果硬要說,真實可能是特別的地方。
新報:有人說你的作品會讓人感到頹廢、喪氣、絕望的負面情緒很多,你對此怎么看?
胡遷:誰說的呢?那你去問問他,每天醒來,臨睡前,或者上班時去飲水機接水的時候,只要他有一瞬間反思過自己,就知道每天都在美化自身的生活。朋友圈發點東西、在自己身上貼標簽,或者手機里攢了幾百張照片等著什么時候給人看。我不是說這樣不好,而真正可貴的事物,是在世界的夾縫中,而不是悲觀在世界的夾縫中。認識到這一點,也許會對整個生命的秩序有由衷的感動。
新報:這本書中,有很多故事都給人很真實的感覺,有哪些故事是真實發生過的嗎,或者你真的經歷過?

胡遷:每個故事會有一個源發點是真實的,故事發展的情感邏輯是真實的,所有的細節是真實的。你可以把它們看作真實的故事,我覺得會發生,而現實中發生的事情比我寫的更有力量。你得使盡渾身解數才能扯開點什么,才能看到一絲自認為的美好之物,但之后,只要你懈怠了,灰暗會重新堆積。《大裂》里面寫的不是青春,是中國大部分大學生,或者叫專科生。人們總是討論白領群體、底層、既得利益者、創業者等等人群,這些標簽下的人在若干年前還是青年時,人們又都統一美化成青春,這是一個錯誤的定義。賴在宿舍每天打游戲,無所適從,不明所以地談戀愛,這個中國龐大的青年群體,不叫青春,這里面有很復雜的東西,復雜得跟加繆的《局外人》一樣。
新報:哪些作家對你寫作的影響最大,文學在你心中是什么?
胡遷:沒讀過非常多的書,喜歡麥卡錫、勞倫斯·布洛克、理查德·福特,他們很美國,美國文學很好。文學對于我是個很安全的出口。本版撰文新報記者回振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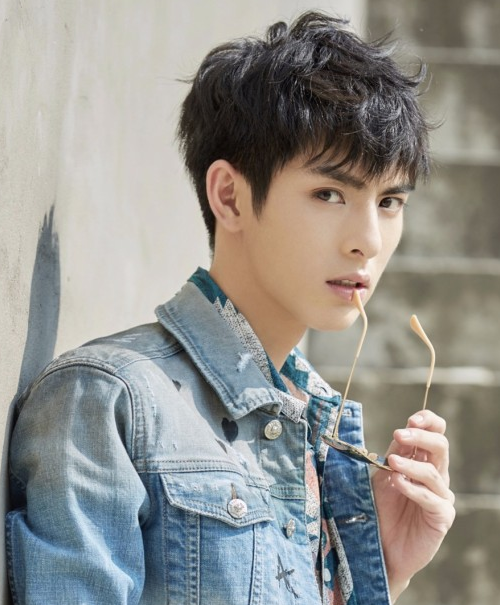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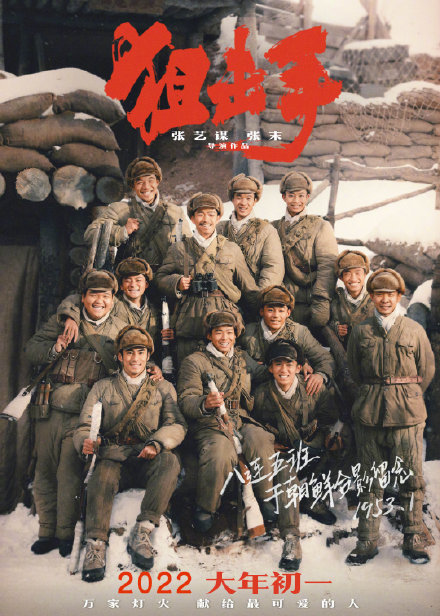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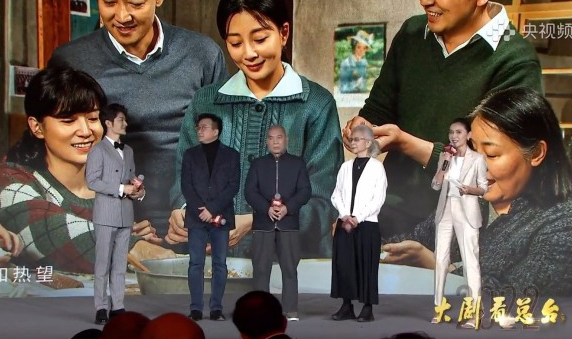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