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人世間》原著:周楠“那死前的一問”,到死都覺得認駱士賓沒錯
文丨卿心君悅
駱士賓的出現,打亂了周家平靜的生活。
為了要回唯一的兒子,他做好了充足的準備。先是利用姚立松與周秉義的關系,打探周秉義與周家的態度,并附上10萬元支票。然后派水自流,找到鄭娟與周秉昆,以為了楠楠的前途著想,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隨后以出國深造為由,利誘楠楠。
最后,駱士賓親自出面,以慈父的面孔向楠楠表達自己的誠意。
可是千算萬算,他都沒有想到,他沒有搶回兒子,而周家也徹底失去了楠楠。
這場奪子大戰中,沒有誰是贏家,楠楠的意外死亡讓這場風波徹底結束。縱觀整個故事情節,在這場生恩與養恩的對決中,所有人都認為自己是受害者。
鄭娟與周秉昆
對于曾經的過往以及楠楠的身世,鄭娟與周秉昆一樣諱莫如深。
如果不是駱士賓的突然出現,楠楠的身世或許會成為一個永遠的,而周秉昆也早已忘了楠楠不是自己的親生兒子。
一旦楠楠真的認了駱士賓,那么鄭娟與周秉昆都將受到極大的傷害。
對于鄭娟來說,駱士賓曾經帶給她的是無盡的傷害與屈辱,讓她一度想要了結自己。她無法原諒駱士賓的罪行,那場被水自流美化成“情難自抑”的傷害,那次差點要了她命的意外,是她一直想要擺的夢魘。
可是,如今那個,想要帶走她的兒子,企圖讓兒子接受他的存在,她絕不會同意。她不愿在兒子面前承認自己曾經受到過的屈辱,也不愿仇人帶走她含辛茹苦養大的孩子,如果楠楠認了駱士賓,對她來說無異于是認賊作父,從此她不得不時時刻刻活在過去的陰影中。
而周秉昆對于駱士賓奪子一事,內心很是。
周秉昆對駱士賓本來并沒有恨,甚至內心深處藏著一絲感恩。在他看來,如果沒有當年的事,他根本不會認識鄭娟,更不會擁有如今一家四口的幸福。
但是,他的這種想法,是基于駱士賓不會再出現在他的生活中。
當他從水自流口中得知駱士賓想要回楠楠的時候,他的第一反應是“他敢那樣,我殺了他”。就像原著中的那段心理描寫一樣:
“他站在里屋炕前低頭看著兩個兒子熟睡的臉,心中忽然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沖動,想要像猛獸般叼起兩個兒子,將他們轉移到自認為絕對安全的地方——駱士賓根本見不得的地方。他太清楚他們這個四口之家缺一不可的關系了。別說在他和鄭娟之間楠楠這個兒子有多么重要,就是聰聰一日見不到哥哥也會魂不守舍的。”
如果楠楠認了駱士賓,周秉昆受到的傷害不比鄭娟少,甚至會更多。
畢竟,周秉昆從一開始就知道楠楠不是自己親生的,但是他心甘情愿地接受,并費盡心思說服父親,抗住了周家所有的壓力。后來,他又視如己出般地撫養著楠楠,十幾年的養育之情付之東流,他能不傷心嗎?
從鄭娟與周秉昆的角度來說,他們確實是奪子風波中的受害者,一旦楠楠認了駱士賓,帶給他們的不僅僅是,還是與傷害,這一點毋容置疑。
周秉昆比鄭娟更難的一點是,他沒法名正言順地不讓楠楠認駱士賓,鄭娟可以以親生母親的名義干預楠楠的選擇,可是周秉昆不能,他是養父不假,但養父又怎能阻止孩子認親生父親呢,即便心里再不愿意,這種話他也難以說出口。
周家人的態度
在周家其他人的心中,楠楠認不認駱士賓并不那么重要,甚至可以用無所謂來形容。他們的原則更偏向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對于周秉義來說,他從頭至尾就沒有把楠楠當做自己的侄子,或是周家的一員。他對楠楠的印象與關注很少,甚至當楠楠親昵地叫他“大伯”的時候,他會產生一種怪怪的感覺,他把這種感覺形容為:
“如同理性的成年人面對自己并不樂于接受的既成事實那樣,做出的反應僅僅是修養使然,而非自然的親情反應。”
抱著這種心態的周秉義,對于駱士賓要回楠楠,并沒有抵觸心理,甚至在他看來,周秉昆為了爭取楠楠與駱士賓結仇,是件愚不可及的事情,一件本可以順水推舟的好事,被弟弟攪成了一件兩敗俱傷的壞事。
至于周蓉,她與周秉義一樣。
周蓉對楠楠的友好,僅停留在表面,取決于與弟弟關系的依托上,她對這個侄子的存在,同樣沒有太多的關注。當她得知楠楠的親生父親想要認回楠楠的時候,她是持樂見其成的態度的。就像原著中寫道的:
“說白了,楠楠是別人的種,而且是強暴所生,有什么可爭的呢?她認為,自己這個姐姐知道真相太晚,如果早知道,她會勸弟弟想開點兒,干脆放棄楠楠這個養子。”
至于周秉昆因為楠楠入獄的事,她更是覺得完全沒有必要,她無法理解弟弟的做法。
周秉義與周蓉,他們都沒有真正站在周秉昆的角度考慮過,完全以一種旁觀者的姿態,看待著事情的發展。當然,他們也沒有向周秉昆表達過內心的真實想法,畢竟如果當面支持楠楠認回駱士賓,自然會讓弟弟感覺到他們不顧親情,愛惜羽毛的他們,不會傻到這種地步。
在他們心中,最要緊的從來不是認或不認,而是不管怎樣,別將事情鬧大了,傳開了就好,否則他們會跟著一起丟人,甚至受到不必要的牽連。
不過,這是原著中周秉義與周蓉的態度,在電視劇中,周秉義沒有站在周秉昆的對立面,而是選擇支持周秉昆的決定。
這是讓我感覺到周秉義很有人情味的一幕。如果他一副事不關己的嘴臉,或是完全理性地權衡利弊得失而支持駱士賓,那么對于周秉昆來說,這個哥哥不要也罷。
親人是榮辱與共的存在,周秉昆想要留住楠楠,并不涉及是非觀念的問題,也不觸犯什么道德底線,僅僅是出于對楠楠視如己出的情感。如果這時周秉義依舊不能予以情感上的理解與支持,那么只能說,他太過冷血薄情了。
楠楠的真實想法
在整件事情中,或許最糾結的是楠楠。
他被駱士賓要送他出國的計劃說服后,便偷偷地趕往機場,準備出國。在臨登機的最后時刻,他后悔了。可是沒有踏上飛機的他,卻再也沒有見到養父周秉昆,那時,周秉昆在與駱士賓在爭執中,失手傷人被抓了起來。
后來,楠楠公費留學去了國外,并對鄭娟發誓,周秉昆一天不出獄表示原諒自己,他就一天不會回國,他用這樣的方式懲罰自己。
在留學期間,楠楠曾去看望過同在國外的周蓉與玥玥,這是楠楠死之前,最后一次見周家人。他曾問過周蓉一個問題:
“我回國后,究竟該怎么對待那個人呢?”
由于不了解周蓉的態度,楠楠用“那個人”代替了“我生父”三個字。
這是自駱士賓出現以來,楠楠心中一直困擾著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其實從他答應駱士賓出國的那一刻起,內心早已有了答案。
駱士賓是他的親生父親,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即便他的這個生父曾經有多么卑劣,但是如果沒有駱士賓,他也就不會存在于這個世界上。
在他看來,自己是駱士賓唯一的孩子,如果他不認駱士賓,才是不孝,畢竟生恩大于天。
他認駱士賓,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與價值。出國是他的夢想,這是周家無法給予他的。在他心中,為了追逐自己的夢想和實現自我的價值,本來就需要付出代價,他因此認下駱士賓并沒有錯。
玥玥曾經勸過他,為了理想出國,等有出息了再回報養父和母親也是好的,他認同這句話。
在楠楠心中,他感激自己的母親與養父,也從來沒有想過,認了駱士賓就不認周秉昆和母親了。但是事實擺在眼前,他得接受有親生父親的事實,認或不認都改變不了。
在他看來,認駱士賓本身是件兩全其美的事,自己既可以實現夢想,又有能力報答養父與母親,為什么別人要拿情感來綁架他,指責他的行為是忘恩負義,可是他并不這樣認為。
這也是當初楠楠決定聽從駱士賓的出國建議時,內心真實的寫照。
在楠楠看來,出身不是他能左右的,母親、養父以及生父之間的恩怨也與他無關,那是上一輩的事。他從來不需要做選擇,因為認或不認,不是他的選擇,而是在得知真相的那一刻就注定了。
如果不是周秉昆因為他而入獄,楠楠并不會覺得自己有錯。他覺得自己才是奪子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以為的生父變成了養父,自己的生父又是母親的“仇人”,他認了生父,別人會說他白眼狼,他不認生父,又會被人詬病不顧生恩是不孝。
對于楠楠的這件事,讓我想起了畢飛宇曾說:“我們處在一個價值的多元化的時代,所謂‘多元’,本質上是我們什么都不相信。”
換個說法解釋,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基于各自的角度所有人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且每個人的想法似乎都是對的,都有其道理,鄭娟與周秉昆如此,楠楠、周秉義和周蓉也是如此。
或許這就是《人世間》的魅力,將人性的與價值觀的多元化一一剖開,展現給我們。
卿心君悅,一位情感觀察者,Ta說書評、影評人。用文字溫暖你,我。
關鍵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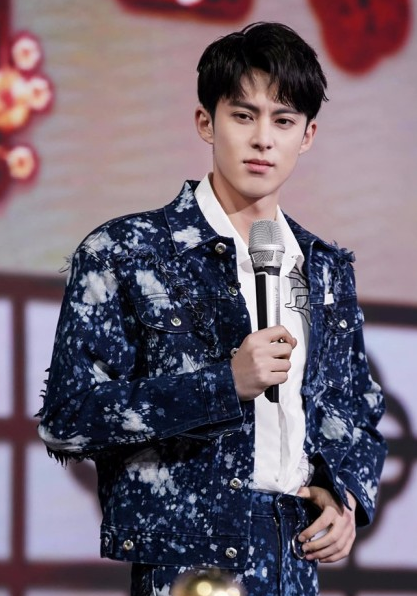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