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曾是天使,后來卻變成了惡魔,關于未成年人犯罪,最近有一部劇做了深刻有力的探討,它就是——
《少年法庭》
這部劇題材十分大膽,直面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從校園暴力到殺人分尸,全方位還原少年犯罪的全過程。由金惠秀、金武烈、李圣旻、李姃垠等戲骨合作,剛開播就在豆瓣獲得了9.0的高分評價。
網飛一口氣直接放出十集,不愧是金主爸爸,劇迷們再也不用忍受每天等更新的痛苦了。
伴隨著如誦經般的配樂響起,夜幕降臨,一位滿身是血的少年在街上尋求幫助——找人借電話。
你以為他是被人傷害了?
不,這是他去自首的路上。
難以想象,這位13歲的少年殺害了一名與他無冤無仇的8歲男童并將其殘忍分尸,兇器則是一把滴血的斧頭。
少年犯罪案件之復雜與棘手,讓韓國為了這些人專門設立了少年法庭。
面對每年三萬起案件的工作量,愿意接手的只有20名法官。
而這起案件之殘忍,引起了社會媒體的大量關注,接手這個燙手山芋的是新調來的法官沈恩錫。
沈恩錫在處理少年案上經驗豐富,手法老練,更重要的是,她對少年罪犯厭惡至極,只要是她審的案子處罰力度常常都在最高級別——十級處分,也因此被冠以十恩錫的稱號,令少年們聞風喪膽。
一審如期開庭,但令人震驚的是,罪犯白成友在闡述案件經歷時不僅沒有流露出一絲一毫的愧疚之情,反而嬉皮笑臉,滿不在乎。
為什么這個少年惡魔可以如此猖狂,因為他深知,按照未成年人保護法,他將會得到和他所做出的傷害極不匹配的懲罰,——只是在拘留所呆上一段時間即可,既不用服刑也無需承擔任何的法律責任,精神疾病的診斷書還可以成為推脫罪行的借口。
連他母親也一臉不在乎的樣子,連出庭時間都錯過。
但另一邊被害男童的母親卻悲痛欲絕,不僅找不回兒子的全尸,連基本的懲罰也無法讓施暴者品嘗。
沈恩錫望著前來求助的被害者母親一遍遍地自責,詢問,哭泣,感受到身為法官是那樣的蒼白無力。
少年保護法為這些殺人犯建造了一個邪惡肆虐的牢籠,卻一刀一刀地劃開無辜者的心肺,讓其承受莫大的痛苦。
她只能不斷地對案件進行復盤,來給被害者家屬一個交代。
而就這反復審查的過程中,沈恩錫發現,思覺失語癥患者的最大特征是無法高度集中注意力,但白有成從殺人到分尸再到拋尸的過程,恰恰需要精神高度集中,思維極度清晰,并且擁有高強的抗壓能力,這也意味著,殺害男童的并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
這竟是一起案中案。
在調取了大量的監控錄像和白成友的通話記錄后,沈恩錫終于找到了同一時間身穿同一服裝的嫌疑人——年滿14歲的韓睿恩。
如果能夠證實韓睿恩就是兇手,那么,這個案子的性質就可以從少年保護事件變為少年刑事事件,能夠讓犯罪少年承擔真正意義上的法律責任,處以20年有期徒刑,給被害家屬一個交代。
沈恩錫連忙把這一發現上報給部長,請求他出派人手抓捕。
但此時部長卻為沈恩錫的發現大發雷霆,不僅沒有接受她的建議,反而斥責她多管閑事。
原來,這位部長因出鏡一檔法律訪談節目而爆紅,成為自由黨選舉的新人選。如果這次轟動社會的案件能夠圓滿完成,將會是一樁大功,助力他順利走上仕途。
在這個關鍵的節點上,部長可不想有什么意外發生,這個案子越快完結越好。
但是,沈恩錫沒有放棄,決定自己親手抓捕。
一場貓捉老鼠的戲份在街頭上演。
沈法官不愧是拼命三郎,冒著著被車撞,被鐵絲劃傷的危險,一路追趕韓睿恩到巷子盡頭,最終將她帶回法庭審訊。
連網吧老板看到都打趣道,這年頭,連法官都要親自出來抓人嗎?
而沈恩錫之所以如此的拼命,除了因為對工作的負責態度,對受害家屬的憐憫之心,還因為,作為一個法官,她深知,法院,理應成為這些孩子成魔的最后一道防線。如果連法律都沒有辦法給他們相應的懲罰,那么他們長大以后,就會更加無法無天,成為無窮禍患。
及時止損,是沈恩錫身為法官唯一能做的事情。
但是,法官畢竟不是警察,即使已經有了充分證據,也無法就此斷定罪犯的殺人動機。法庭審訊上,韓睿恩的律師利用她的被害妄想癥診斷書試圖為他開脫罪名。
而白有成也一口咬定他自己并非殺人共犯,而是受到韓睿恩的指使才做出這種行為。
這樣一來,兩人的處罰都會減輕許多。這讓法官們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如果,讓孩子們互相揭露對方的罪行呢?休庭間隙,沈恩錫向左陪席提出了自己的思路。
沈恩錫利用孩子們脆弱的心理防線和自保欲望,激怒白有成讓他為自己辯解,引導他將罪責全部推到韓睿恩身上,而韓睿恩自然也不甘示弱,立刻說出是白有成教自己殺人分尸的事實。
原來,他們彼此為網戀情侶, 在韓睿恩因惡作劇殺人后,白有成教韓睿恩殺人分尸,然后再利用法律漏洞出面頂罪,企圖瞞天過海,讓兩人都可以成功逃脫罪罰。
在一旁聽著自己孩子死前痛苦遭遇的母親終于忍受不住,開始嚎啕大哭,有的孩子是母親的貼心棉襖,而有的孩子卻可以如地獄里爬出來的惡鬼一樣可怖。
在他們手起刀落,把內臟一塊塊挖出來的時候,是否有想過他的父母會有多痛苦,是否有想過將來他們也會可能有這樣可愛的孩子。
“請法官務必嚴懲,不要再讓這種憾事發生”,不要再讓更多的孩童受到這種傷害,被害者的母親在法庭上提出這樣的請求。
最終,經過三名法官一致協商,決定判處協助殺人的白有成最高處分,拘留兩年,而殺人主犯韓睿恩,則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少年刑法的最高懲戒——二十年有期徒刑。
審判結束,沈恩錫將之前被害者母親為自己做的便當送了回去,里面裝著的是前一天晚上自己親手做的小菜,這無言的回禮中,仿佛在與被害人母親訴說,我沒有辜負你的訴求。
但是,這兩位少年是否真的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和教化,沒有人能夠保證。
沈恩錫能做的只是在法律允許的最大限度里給予他們教訓,但是死去的孩童再也無法回到父母身邊。
正如白有成的母親前來質問法官,為何自己的孩子沒有殺人卻還要承擔處罰,沈恩錫看著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問道,“白有成九歲的時候,你為他做過什么,但尹知煦(被害者)九歲的時候,卻永遠無法見到他的父母了,因為你的兒子的關系,就在你家里死去。”
少年案件啊,處理的再多,也還是難以適應,它們總是讓人覺得心里不痛快。
處分的對象明明是少年犯,但是那把十字架,卻要毫不相干的人背負一生,是融進骨血里,每當看到街上玩耍的孩子,吃到自己曾經為孩子準備的飯菜,都會想起來的切膚之痛。
父母缺乏管教,社會缺失教育,法律布滿漏洞,從一個個可悲個體背后映射出的,是整個社會對于問題少年的態度,是環境,給了邪惡滋生的溫床,等他們服刑完畢,長大成人,然后呢?
這是沒有一場沒有答案的追問,沒有結果的審判,在家屬,律師質問法庭的同時,是否也應質問他們的監護人,教育者,和這個社會,他們為這些孩子,做過什么呢?
這部劇題材灰暗,少有人涉足,但它又這樣真實地存在,甚至某些劇情就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而成。
每一集都是淚流滿面地看完,但卻沒有宣泄的快感,仿佛被人扼住咽喉,千言萬語化作一句嘆息, 與其說它值得,倒不如說它應該被看見,把糜爛的腐肉暴露于陽光之下,才能去腐生肌,枯木逢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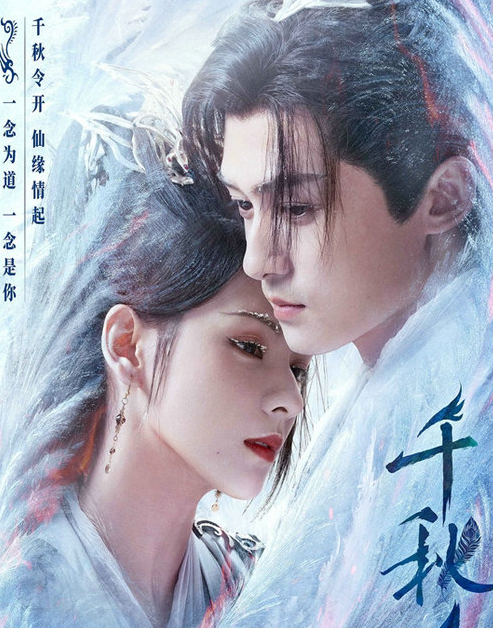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