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華裔導演石之予的新作、皮克斯出品的影片《青春變形記》悄然走紅,引發了多輪討論。影片圍繞著一個亞裔女孩展開。美美向來是一個乖馴優秀的“別人家的孩子”。在13歲的某天早晨,她發現自己突然變成了一只紅棕色的小熊貓。
觀眾和美美一起逐漸認識到,這種變成小熊貓的能力其實是一種家族遺傳:在美美的家族里,所有的女性都會在青春期不受控地變成小熊貓。而這種不受控的起因,往往是極端的情緒:憤怒、羞愧、渴望……她們共同面對降服心中這只小熊貓的難題,并力圖把它封印在鏡中。
《青春變形記》劇照。
實際上,當我們把目光投向銀幕,都會發現屬于我們的那只棕紅色小熊貓。終其一生,人們都在反復調試、校準對于自我和他者的認知。
而《青春變形記》所承載和引發的討論,還與風起云涌的身份政治相關。在本文作者看來,近年來諸多電影——比如《摘金奇緣》《花木蘭》《包寶寶》,甚至不久之前上映的《雄獅少年》——都引發了相似的爭議。在這一語境之下,《青春變形記》讓我們看到了在滑入刻板印象之前,剝去身份政治的標簽之后,觸摸到真實成長經驗的可能性。
《青春變形記》無疑是在最近國內院線之外,討論度最高的電影之一。在觀看影片之前,就有三個不同的朋友詢問過我:你看過那個拍小熊貓的動畫了嗎?
《青春變形記》劇照。
《青春變形記》中的4 TOWN演唱會。
《青春變形記》劇照。
然而,《青春變形記》里的母親并不是一個反面角色。她和青春期到來前的美美相處融洽、彼此信任、互相關懷。甚至,對于月經初潮,這個同樣在社會層面上有敏感性的因素(片中同學們看到衛生巾時的震驚、別扭可以證明),她也表現得準備充足,時刻可以給予女兒指導和關懷。
《青春變形記》中變身后的媽媽。
自我,不僅僅作為對立面而存在
《包寶寶》劇照。
到如今,身份政治越來越成為一種創作和解讀文藝作品的重要維度。于是像《摘金奇緣》《花木蘭》這樣的作品,都多少因為涉及文化挪用、刻板印象而遭遇批判。在這種情況下,《青春變形記》的選題不能不說是敏感的。但從目前的反饋來看,觀眾給予這部電影的評價多是真誠和溫和的。
《青春變形記》確實有遠超《摘金奇緣》類亞裔電影的真誠細膩。這種真誠主要還是來源于不預設一種東方和西方之間的對立。《摘金奇緣》雖然是全亞裔卡司,但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扮演著高知灰姑娘角色的女主角顯然浸潤著美式的個人主義,而男主角位于東南亞的豪門大家族則示范了一個再標志不過的,講求家規森嚴、門當戶對的“想象中的東方”。在這個東方的大靶子之上,插滿了由大洋彼岸射來的象征“現代文明”的箭雨。
無論東南亞的大家族被塑造得如何富貴,而女主角如何窮酸,這種價值觀上的力量不均仍顯而易見。最重要的是,這其實不是一場個人和家庭的斗爭,而是西方和東方的斗爭。
一如薩義德最著名的概念東方主義(Orientalism)所示,很多語境中,東方只是一個想象的影子,被建構為異質的、分裂的、他者化的、作為與“us”(我們-西方)對立的“they”(他們-東方)而存在。這并不意味著《摘金奇緣》中的東亞大家庭沒有折射出任何現實的影子,就像刻板印象并不意味著純粹的虛構。只是這樣的東方只是一個永恒的客體,只為了證明并強化西方的自我而存在。東方是被定義、被注視、被描繪、被崇拜、被挑戰的,但唯獨不是親口說話的。
《摘金奇緣》劇照。
在影片的高潮部分,美美面臨著最終選擇。是否放棄小熊貓?是否放棄這樣異形、怪誕但真實的自我?創作者把這樣的抉擇視覺化成這樣的圖景:美美努力地鉆進鏡子,而小熊貓逐漸從她身上剝離下來。她回頭看,與鏡子那頭的小熊貓對視,而她們的身體緊緊相連。
更容易被忽略的是,在美美的故事線上,母親可能是所謂的“個體必須反對的對手”,但在母親自己的故事線上,她也擁有著自我,且也經歷過在鏡中,和小熊貓四目相對的那一刻:母親的小熊貓甚至在體形上比女兒的更大。在這個層面上,《青春變形記》比《包寶寶》更進一步:后者的和解只建立在割舍不掉的血濃于水之上,而前者真正回溯到了母親的童年——方知這些掙扎和恐懼,其實都能沿著家族樹追溯到幾代之前。
《青春變形記》劇照。
所以其實《青春變形記》講的不是一個關于內和外的故事。同樣含有動物/非人類作為主要元素,它并不像《忠犬八公》《超能陸戰隊》那樣塑造一個無私的非人類角色以和人類相對立;同樣講述東亞的故事,它也不像《摘金奇緣》那樣塑造一個傳統的東方以和西方相對立。
刻板印象?
在文章的尾聲,我想回來談一談上文略過的《包寶寶》曾遭遇的爭議。其實這也是《青春變形記》現在收到的反饋中,雖然占比較小、但仍然存在的一部分。
《雄獅少年》劇照。
我們面對的仿佛是一個極度割裂、充滿不信任的環境。它索求一種不可思議的剖腹自證,唯有如此才能證明作品中的某些特征(尤其是負面特征)是出于真誠還是包藏禍心。但實際上,被一部電影仿佛天塹一般隔開的,處在創作和接收兩端的創作者和觀眾,也許擁有一個共同的、較為理想的方向,那就是放下強烈的對立思維和標簽概念。
我并不反對身份政治,實際上它也構成了我看世界、看電影的一種維度。使用這個工具,你會發現某些群體在大銀幕上長達數十年的缺位、噤聲、弱化、客體化,而這些在從前看來只是渾然不覺。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也并不被現在的身份政治嚇退,認為就因為所謂的政治正確和投機者的存在,我們不可能再看見真誠自然不別扭的好故事了。影視創作者并非被身份政治戕害的無辜受害者。他們塑造的電影景觀也需要對現實環境負責,而不是成為“干凈無菌樂園”。就像我很喜歡的導演林嶺東在拍完《學校風云》后所說:“作為導演一定要有社會責任……拍電影的感染力很大,有時候要收著點,否則這樣拍下去,世界會變得亂七八糟!”
如上文所述,《青春變形記》就是我認為的,在新時期講述一個少數族裔故事的積極嘗試。它不是一部滿分電影。誠如一些評價中提到的,它對于親子關系的描寫還不夠深刻,缺乏像《頭腦特工隊》《心靈奇旅》等皮克斯系動畫那樣,完全打破子供向限制的決心。但不妨礙影片的主體仍然是好的,好就好在它彌合傷口,而不是創造或撕裂傷口;承認和展示特殊性,而不是抹平或者構造特殊性。無論是在個人的維度還是在社會的維度,無論是在電影內還是電影外,它都更像試圖搭建一道橋梁,在自我和家庭之間,在想象中的東方和西方之間。所以站在你面前的美美,能發出她自己的聲音。
《青春變形記》劇照。
正如影片中展示的,處于自我糾纏中的人不僅有美美,也有她的母親。終其一生,人們都在反復調試、校準對于自我和他者的認知。影片之外的觀眾也不例外。當我們把目光投向銀幕,就像把視線投入鏡中,偶爾也有機會看到屬于我們的那只小熊貓。而那個時候,如何面對和處理這只小熊貓,就是作為觀眾的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作者 | 雁城
編輯 | 走走 青青子
校對 | 賈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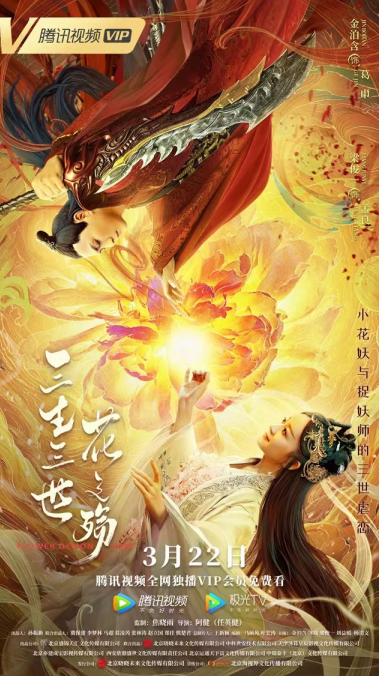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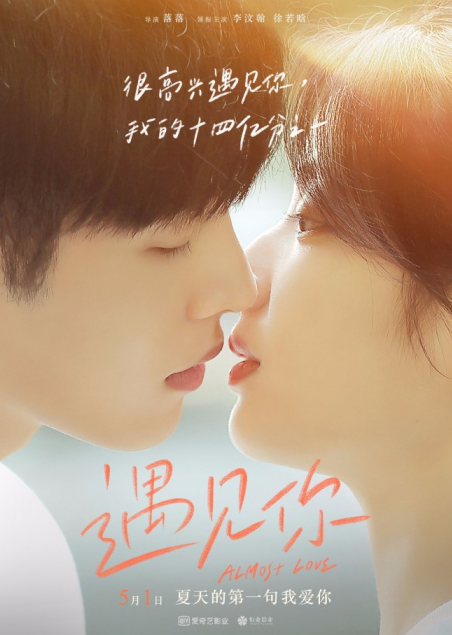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