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們常說這個時代好電影太少。
或許只是缺少發現好電影的眼睛。
3月被引進大片霸屏的院線,一部首日排片僅1%的小眾紀錄片殺出重圍,斬獲豆瓣7.6的高分,僅次于《新蝙蝠俠》。
這部不起眼的紀錄片,比商業大片更有“被看見”的價值。
“煉”愛
《“煉”愛》聚焦五位都市單身女性的情感困惑。
導演董雪瑩也是女性,她的劇情片《入戲》曾經入圍41屆哥德堡電影節和第12屆 FIRST青年影展。
《入戲》
早在公映前,《“煉”愛》已經在上海國際電影節、北京國際電影節等影展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煉”愛》的英文譯名為《Hard Love》,“煉”是“戀”的諧音,也意味著燃燒與鍛造的過程。
導演在采訪中這樣解釋片名: “我們每個人在情感的道路上都經歷過各種挫折,有的人一蹶不振,把自己保護在一個殼里,不再相信愛。但也有的人浴火重生,繼續尋找真愛和溫暖。”
影片選取了五位不同背景,卻同樣“相信愛情“的理想主義者。
用溫柔的鏡頭撕下她們身上的“剩女”標簽。
于是我們得以看見一群鮮活有魅力的個體組成的都市女性群像。
農村出身的北漂白領,紅梅,她努力上進,從農村考上大學,靠奮斗留在大城市。
家庭條件良好的北京土著,Kitty,酷愛Hello Kitty玩偶,公主心爆棚。
自由浪漫、多才多藝的文青,月兒,金句是“女人一定要綻放”。
事業成功的“女強人”談婧,理性大于浪漫,松弛且自信,在尋找“同路人”的道路上,她拒絕為愛情放低姿態。
還有獨自撫養女兒的單親媽媽,李桃。一個十八線演員,曾經也有大明星的夢。如今,為了陪在女兒身邊,她轉行女主播,每天連續直播六小時,說到嗓子干啞。為母則剛的堅韌,在她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
《“煉”愛》是一部女性主義視角的作品,對兩性采取了平視的態度。
雖然沒有刻意丑化男性,但影片中的男性,確實不如女性可愛。
即使不是作為戀人,只是作為異性朋友,他們由于身處男性視角,對女性困境缺乏基本的共情與反思。
要么熱衷嘲諷說教,談婧的朋友暗示她單身是因為眼光太高,能挑的人又太少。
要么有性別刻板印象,紅梅的哥哥聽說妹妹想找物質條件比自己好的,不由分說把她定義為“物質女”。
男性對“愛情”的理解也比女性更現實,更受制于性別刻板印象。
有人喜歡快餐式愛情,認為性重于愛。
有人認為女性應該讓自己浸泡在感情里,仿佛理性的人沒有能力去愛。
大多數時候,他們對單身女性友人流露出的態度是:大齡單身是一種“非自然狀態”,單身的人自己也有問題。
要么個性太強,要么眼光太高,要么……
說得難聽點就一個字——“作”。
女性擇偶困境背后的性別和年齡歧視,被粗暴的標簽掩蓋。
提供的脫單策略無非是勸她們放低標準,做出妥協。
女性豐富的生命體驗,作為人的價值,被排在婚姻之后。
如今的婚戀市場中,人人都是由條件組成的商品。
但不可否認的是,女性往往是被挑揀更多的一方,也面臨更嚴格的“凝視”和篩選。
似乎向下兼容是她們獲得“幸福”的唯一途徑。
除了外部壓力,傳統和現代的婚戀觀在她們身體內部對抗。
一方面,她們是有一定物質基礎,能夠養活自己的“獨立女性”。
對愛情不愿將就、精神需求高。
另一方面,她們仍然被傳統觀念困住。
年齡焦慮如影隨形。
雖然能享受單身的快樂,但依然渴望一個“家”。
雖然堅守理想主義的愛情,但也看重現實因素,把婚姻當成階層流通的渠道。
雖然女性意識部分覺醒,愿意自我奮斗,但”男強女弱”的傳統關系模式還在影響她們的擇偶觀。
紅梅希望另一半可以“依附”,Kitty對男女分工延續了老一輩的看法,做家務也不忘自我調侃:“這么會收拾有什么用,也沒個男人讓我替他收拾”。
生育焦慮也是一個方面。
談婧害怕錯過最佳生育年齡,遠赴國外凍卵。
愛情可以等,身體卻不能等。
難得的是,影片中,這些焦慮的情緒沒有被處理得苦大仇深,反而在日常化敘事中變得輕盈詼諧。
比如,Kitty的朋友和導演打趣她:“你們算是找對人了,跟拍她可以跟拍好幾年。”
比如,月兒的小姨,從國外回來,思想開放,渾身散發著中老年女性的自信光芒,簡直是《致命女人》中的劉玉玲的現實版,她在飯桌上向外甥女“炫耀”,自己這把年紀了還被美國小伙子追著表白。
比如紅梅和哥哥,一個大齡單身,一個離異帶娃,兩個人因為“物質女”的話題吵得不可開交,老父親走過來一句話打斷他們:“兩個失敗者吵什么吵”,化解危機的同時令人會心一笑。
這是劇本寫不出的真實的生活。
影片中有一個情節,談婧說自己寫了一個故事:一只兔子從戰場打完仗回來,掉了一只耳朵,從斷耳處長出了尖尖的刺,后來,她變成了一條龍。
在女性的一生中,婚戀問題總會在某個階段困住我們,但只要放下“為愛而愛”的執念,就會發現人生是如此遼闊。
本文圖片來源于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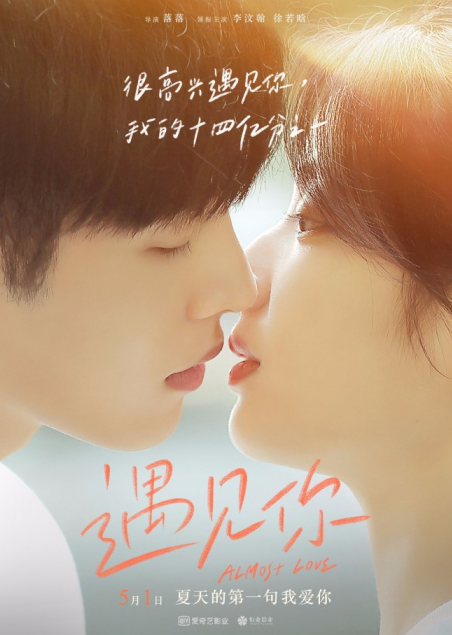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