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西米亞狂想曲》能夠登上內地大銀幕,對于中國影迷來說可謂近距離感受皇后樂隊現場魔力的難得機會。為了凸顯影片的音樂元素,內地引進版甚至特別制作了“卡啦OK版字幕”,方便影迷和歌迷可以邊看邊唱。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的確,作為傳奇樂隊的傳記類影片,把樂隊的經典歌曲作為電影原聲本無可厚非。而且影片還利用大手筆,高度還原了那場振奮人心的世紀經典現場演出,復刻了21分鐘的高潮段落,帶觀眾回到那個神奇的深刻。
《波西米亞狂想曲》依靠配樂創造了敘事連續性。但影片的成功離不開男主角的扮演者拉米·馬雷克的精湛演技。他成功的表現了人物脆弱、敏感,同時兼具狂妄、自大的一面。整部影片,不光是皇后樂隊的成長史,同時也是主唱Mercury不斷尋找自我的認知之旅。
配樂作為電影重要的元素之一,不光具有“聽”的功能屬性,它同時還為看提供了暗示,成為推進敘事的重要一環。音效可以暗示延伸聽覺上的隱喻,可以給影片增加其他方法難以實現的多層次含義,甚至可以標志特定的事件或人物,精心設計的音效完全可以像對白和畫面一樣,成為有力的敘事工具。
《極盜車神》
國內外上映后好評如潮,影評家一點不吝嗇的給予了這部導演處女作一致贊美。《極盜車神》在類型上和《速度與激情》有重合,飆車加上警匪元素的類型片套路并不算創新。但《極盜車神》的配樂可謂全片最大的亮點。影片靠著貫穿全片,沒有一絲停息的配樂,給一幀接一幀的畫面灌入了流動性的質感。開片時,在音樂中,我們看到男主角baby跟著音樂節拍摸著方向盤,利用雨刮器打著拍子,搖頭晃腦甩甩腳,一副沉醉其中的樣子。
影片中,連愛情戲碼的上演也依靠音樂來烘托。可以說,音樂和音效是《極盜車神》極具靈氣和流動性的關鍵因素。賽車的引擎聲浪加上多變的配樂,難怪該片會讓影迷耳目一新。
《生于藍調》
伊桑霍克,那個出演了話嘮三部曲(“愛在”三部曲)的文藝男首次化身美國傳奇音樂家,爵士、cool小號手查特貝克,給我們帶來了動人的《生于藍調》。
BLUE其實不能直譯為爵士,BLUE是憂郁,一種帶有病態,傷感,但卻有著讓人不能自拔魔力的感覺,它是一種不同于平常的狀態。《生于藍調》不同于常規的傳記電影,它采取了黑白與彩色,虛實相映的方式進行敘事。
影片利用光影交織和柔美的配樂精準的表現了查特貝克在毒品和小號,欲望和音樂中的病態美感。一車,一人,一把小號,背后是無限寬廣的大海,壯美的落日之下,查特貝克忍著牙疼,獨自吹著內心的苦楚。
自信的長鏡頭,精美的構圖,把查特貝克一個人烘托得魅力非凡。那場重要的演出,四目相對,眼波流轉,他用一曲myfunnyValentine,打動了所有人,她被他感動的淚流滿面,是愛情讓他如獲新生。
無須摩琢,他自身即是’特殊的存在”。他自己,就是一種聲音。
《初戀這首歌》
從流浪歌手到青年音樂制作人,又到小孩子的談情說愛。約翰卡尼電影的配樂都充當了重要的電影元素。這部電影讓你跟一群小屁孩,搖頭晃腦,甩甩腳,有笑有淚的動情度過90分鐘。
《SingStreet》翻譯成《初戀這首歌》或者《唱通街》。講述一群小屁孩組成樂隊,通過音樂改變自我,贏得尊重,找回人生,尋求夢想的簡單故事。
影片的劇本其實非常簡單,但可貴的是,所有敘事的節奏點和推進幕全都靠音樂來執行。
每當康納和拉菲娜的關系發生轉折的時候,新的歌曲被康納創作出,歌詞和音樂清晰的表達出了角色的情緒和故事的走向。“Happy-sad"成為他們歌曲的主要風格,就像生活一樣,快樂與悲傷總是相互纏繞。看似歡快的歌曲風格中隱隱透著悲傷的氣息。
不光是初戀這回事兒。其實電影通過音樂還描繪了一幅生活的橫切面。康納通過音樂在學校找回了自信。面對曾經欺負他的暴力狂,他挺直了腰板說出:你的暴力世界里有我,但我的世界里絕對沒有你的存在。
《冷戰》
88分鐘,無一處“廢筆”,囊括了意識形態、冷戰、音樂和愛情,收筆時以極為震撼的結尾,一劍封喉,不給人絲毫喘息機會。《冷戰》是一部精致的電影。影片講述了波蘭流浪藝術家維克多和他心愛的歌者祖拉之間長達15年的愛情糾葛。
影片最更可怕的地方是,整體來看,導演帕維烏·帕夫利科夫斯基從音樂入手,架構了其與時代背景和政治話語之間的關系,而且基于音樂設計了鏡頭調度乃至整個視覺體系。這也是為什么《冷戰》時長雖段,但非常耐看的原因。
你根本不需要刻意去夸獎影片的配樂,從一開始的鄉村民調,自然樸實;到斯大林時代,歌曲被意識形態化,群舞大合唱代替了從前的純真;
兩人到巴黎時,醉人碎心的爵士樂此起彼伏;
片尾那個空鏡頭,幾乎完全靜音,一陣微風吹過,搖曳了草苗,往事隨了風。就像《冷戰》精美的宣傳手冊上寫的那樣:愛情是愛情,僅此而已!
《馬戲之王》
作為歌舞類型片,《馬戲之王》的IMDb評分甚至擊敗了《愛樂之城》,還有老牌經典《芝加哥》。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馬戲之王》就講述了P.T.巴納姆在成為“馬戲之王”前從做夢到造夢的勵志故事。作為歌舞片,《馬戲之王》絕對是一部在視覺和聽覺上都能征服人的佳作。也影評人質疑片子的故事太過簡單,但一旦談及視聽效果都對會對其贊譽有加。
導演格雷西希望通過歌曲來講故事,立人物,起沖突。片頭曲《最精彩的演出》寓意馬戲人生的開始;《一百萬個夢想》則表現著一種挑戰和反抗精神;《重獲新生》是巴納姆開始實現目標,為單調的人生增添色彩的轉折時刻;而那首《從今以后》是關于尋找救贖。
能夠讓觀眾耳朵懷孕的配曲,在舞蹈的精心設計下,讓影片將當代與古典融合得天衣無縫。歌曲通過臺詞和旋律賦予了影片核心和靈魂,讓觀眾聽得出、看得懂那些情感的高潮和低谷,以至于能夠地抓住影片傳達的主題和精神。
《馬戲之王》讓人們相信歌舞類型片可以實現其他藝術形式不能實現的效果,那種難以言表的情緒、直擊心靈的瞬間,可以通過音樂準確的傳遞到觀眾的腦海里,內心中,而且它還使用的是通俗易懂的流行音樂。
《閃光少女》
《閃光少女》中最有意思的設定無疑是東西方音樂的碰撞。女主角在讀的民樂系一直被隔壁的西洋樂系看不起,一直被認為是野路子,沒有前途。
多股壓力,讓民樂系學生徹底站起來反抗。而雙方較量的方式,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斗琴!在重量級客串演員陳奕迅飾演的教育局領導的巡查過程中,民樂系學生隔著那扇為了保護西洋樂系學生練習不被打擾的,帶有偏見的鐵門前,以樂會友,以樂器作為武器,開始較量。
雙方學生你來我往,靠技藝傳達對于夢想的堅守。這場戲,不光展現了中西音樂的各異,同時也表現了中西音樂融合的可能。陳奕迅飾演的領導也扣題的說出,音樂不該有階級,樂器之間沒有貴賤,中西樂完全是可以融合的。
中西音樂之間的對抗是主線故事中最明顯的沖突呈現,以此主題脊梁,其實《閃光少女》還暗含了二次元和現實的對抗,家長對于孩子教育方式的對抗,夢想和現實等多組沖突主題。以音樂包裹著青春,加上二次元元素的點綴,通過在對抗中達到最終的和解,找到自我的夢想,得到真愛。這太符合青春的設定了,這就是所謂的“沒有無法原諒的敵人,只有茁壯成長的自己”。
優秀的電影絕對離不開好的音效以及配樂,觀影時如果將聲音關掉將令影片的魅力銳減,其蘊含的情感沖擊力也會被大大削弱。所以,電影敘事從來都無法離開那些“看不到”的東西,有時候那些聽得到東西就是電影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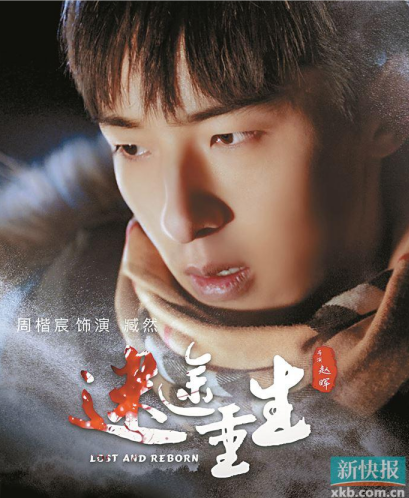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