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戈達爾去世的消息,讓很多人陷入懷舊情緒當中。
大家紛紛開始懷舊——試圖回到過去,回到新浪潮,再不濟回到18年那場驚奇世界的戛納直播也好。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當“懷舊”成為一種集體情緒,它背后的邏輯也不言而喻,追憶電影往日的榮光,似乎也變成一種療愈。
就在前不久結束的北影節上,除了經典修復的《綠洲》外,還有一部來自韓國的新片,就講述了一個關于電影的“老”故事。
《致敬》非常的不起眼,沒有名導明星,妥妥的小眾、小制作。
居然在豆瓣拿下了7.9分,賺走許多觀眾的眼淚
有人說它是女版的《一秒鐘》,同樣關于電影本身,關于每個觀眾心底里的迷影情節。
在主人公的選擇上,讓多個時空的女性命運重合在一起,又有了點兒《時時刻刻》的意思。
故事圍繞著一位事業不順的中年女導演金智婉展開,看她如何在一次膠片修復工作中,誤打誤撞的與韓國第一代女導演展開隔空對話。
所謂的“致敬”,在本片中既指前輩,也指時代,更指的是電影本身。
當然,這樣的故事設定算不上新鮮。
就視聽和劇作結構而言,本片也并那么突出。
甚至是片中反復出現的一些意象,比如落灰的蛛網、待割掉的子宮、前輩女導演墻上的疊影等等,都有些直白甚至是笨拙。
但你還是會被感動,也一定會被感動。
《致敬》這個片名起的宏大,但起筆和落腳處卻無比的小。
它并不貪心,僅僅注視著一位“拍電影的大媽”金智婉,盡其所能的克制、謹慎,遠離一切廉價的煽情,也避免吵鬧的控訴。
最后會打動你的,是一種憨厚且純粹的熱愛,它關于電影,也是每一個女性創作者的自白。
其實,了解一下導演申秀媛就會有跡可循,故事里的主角就像是她本人的一次延伸。
在如火如荼,人才輩出的韓國電影圈里,申秀媛名不見經傳,不溫不火的堅持拍片,也默默的堅守著一抹平靜的女性視角。
(申秀媛)
自己掙扎在妻職、母職夾縫中的創作欲,似乎反向成為一股動力,推著她一直走到今天,拿出了《致敬》。
在這部談不上多驚艷的新作中,你很難苛責導演的苦心。
它本質上其實是在給自己打氣——“拍下去吧”,畫面上的點點滴滴分明也來自生活本身。
這次的劇本有了明星的加持,女主角是在《寄生蟲》《少年法庭》《哭聲》中,像變色龍一樣的女演員李姃垠,在片中成了導演的分身。
她穩如泰山的表演,淡化了劇本在情節上的設計感,也過濾了那些流于表面的抒情。
中年女導演金智婉的故事,從蝸居開始。
在泳池里,她浮沉著略有些肥胖的身軀,偷偷許愿自己的第三部電影《幽靈人間》,票房能過30萬韓幣。
也就是大約有20個人買了票,便心滿意足。
說得好聽點她是導演,但事實是,十年間一無所獲,全靠丈夫補貼。
只有少女變大媽,面前的好大兒還在幻想著母親能掙大錢供他。
一切都不溫不火,如果把丈夫的牢騷左耳進右耳出倒也能勉強堅持下去。
但拍到了第三部電影,就和“幽靈”這個片名一樣,金智婉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疲乏、倦怠。
影片的推進無比平淡緩慢,我們看著自詡大媽的女主角,面無表情的發呆,遲滯。
也許是更年期的來臨,一貫封閉的她,內里終于開始瓦解動搖。
小區里陌生女人燒炭自殺的新聞,也讓她心有戚戚,難以自抑地投射自己。
“是不是該放棄了”——幽靈般的自我懷疑,就出現在這微妙的“第三部”之后。
此時,一個膠片修復的工作,讓她暫時逃離了自憐的情緒。
而這部待修復的電影《女判官》,就出自韓國第一代女導演洪在媛之手。
《女判官》故事的原型則是韓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法官。
隨著修復工作的展開,三個不同時空的女人,以電影為切口重合在一起。
故事的情節并不復雜,劇情的走向也很好猜測。
甚至她們的困境也如此相似,但也無比雄辯。
尤其在這個大環境中,影片并無控訴感的個人視角,反而變得切題起來。
女性影人的處境和電影的處境殊途同歸,都在時代的風口浪尖搖搖欲墜,看著一輪輪的熱愛和失望輪番上演。
片中,《女判官》因為彼時韓國電影對“女人抽煙”的審查,缺失了部分膠片。
在尋找的路上,金智婉也面臨著兩重“閹割”——在家里,她要剝除創作者的那部分,盡量做一個賢妻良母。
對外,她則最好像個“brother”,才能全情撲在工作上。
從金智婉看似“不成困難的困難”中,你能順理成章的推導出無數被遮蔽的女性聲音。
這種天然的“閹割”,放在中國電影的生態環境中,也更加讓人感慨。
越過我們都能細數一二的行業性別歧視,金智婉站在這樣的處境中,更深刻的感受著“電影”大廈傾頹的危機。
“拍電影十年了,總該掙點錢了吧”
“放棄電影,做生意吧”
曾經杰出女導演被閹割,當代的金智婉如“幽靈”般漂浮在行業邊緣,目擊著金玉其外的假象。
就和曾經的片場不歡迎女人一樣,她也率先在冥冥中感知到一種電影本身難以挽回的衰頹。
在塑造出這一整體性的抑郁之后,導演才吞吐出一些獨屬于女性的困境。
在演員李姃垠幾乎面無表情的表演中,你能看到日常如無形的小錘,如何滴水石穿的擊破金智婉的盔甲。
她處在一種難以逃脫的道德折磨中,展開了自我詰問:
“難道夢想真的比母職高貴么?”
你會發現,片中為數不多的幾個角色,兒子、丈夫、婆婆,見到金智婉的第一句話都是:“快去做飯。”
無論是長大成人的兒子,還是人到中年的丈夫,都在抱怨式的等待著一位長期“缺位”的女人,為他們凋敝、殘喘的人生“重整山河”。
兒子會責怪家里“像旅館”。
丈夫會委屈且憤恨的表示“我都活成什么樣了?”
如果要為此歸因,答案一定是“不務正業”的金智婉。
有趣的是,在修復膠片的過程中,金智婉的處境也數次和老導演、女法官重合。
在60年代,導演洪在媛隱瞞了自己有女兒的事實,只為規避職場風言風語的指責。
在膠片里,女法官的丈夫干脆成了智婉老公的嘴替,控訴著妻子的失職。
其實仔細看來,女主角金智婉和以上兩個形象都略有不同。
她并非一個典型的女強人,更多是一個啞口無言的失敗者。
靠伴侶養家,會從老公的錢包里拿錢,總是照單全收家人的指責,但這種憨憨的“沉默”,反而讓這個形象更多了幾分味道。
它一方面當然指向電影產業的現狀。
底氣不足,外強中干,高不成低不就。
無論是下沉成商品,還是形而上為純粹的藝術都很尷尬,負隅抵抗著流媒體、審查、票房的各方掣肘。
另一方面,它更揭露了一個事實。
那就是“母職和夢想”本不該成為一道選擇題。
在對女性的描述中,我們通常不會贊頌追夢者或孤勇者,即便是贊頌,前提也是不拖累任何人,不耽誤母職和妻職。
把這樣的體悟敘述得如此平靜,大概率都來自導演申秀媛的自我和解。
而治好她“精神內耗”的良藥恰恰是電影本身,這也是影片最純真的地方。
片中的金智婉人到中年,還一事無成。
她無數次的嘟囔“我真害怕寫東西”,但又隨時帶著老花鏡把一切當成素材記錄。
當日常瑣碎、嘮叨、下水道的泡菜渣不斷的消耗、折舊她時,創作的確是一個任意門。
但她也常常感到幾乎惱人的平凡,劇本怎么修改都很一般。
創作的路走得艱澀無比。
同樣,第一代女導演洪在媛也在給友人的信中說著“不知道我是誰,也不知道電影是什么?”
無論夾在劇本里的老照片有多神采飛揚,拍到第三部就戛然而止的創作生涯還是宣告著一股讓人心驚肉跳的無力感。
她們都不是天才,不是才氣四溢的戈達爾。
大多數人都是笨鳥,只憑一點熱愛努力飛到了中年。
但只要嘗過一次創作的甜頭,就扎在電影里,等待它的洗滌,等待施予,再給出自己小小的,微不足道的奉獻。
這也是為什么,這部看似平平的電影,會迎來如此多的好評。
我們已經不可避免的意識到某種堅定的、純粹的,昨日世界的遺產逐漸遠去。
片中曾經熒幕上的男演員,蜷在輪椅上遮掩自己塌垂的面部,不愿示人。
那個時代唯一的女剪輯師,曾經橫眉冷對一切行業陳規,現在卻老的記不起“film”這個單詞。
在馬上被鏟平的舊影院里,放映員上一部充滿激情的手繪海報還是《賓虛》。
60年代名流薈萃,容納多少高談闊論的咖啡館,現在獨留老板一人,他直言著:“我太老了。”
“大家都死了,我也該死了”
在我們的世界里,戈爾巴喬夫去世、女王去世、然后戈達爾去世…
那句振聾發聵的“電影,每秒24格的真理”在社交平臺上被瘋狂轉發。
曾經我們確實對此深信不疑,但昨日世界的遺產確實開始被全面清算,緩緩合上了它的尾頁。
片中的一切都在搖搖欲墜,荒廢的電影院,拿來做帽撐的膠片,空無一人的放映場,票房慘淡的新片。
制片人那句“明天我們的電影沒有排片了”簡直像是未來飄回的魔音。
正是在這種情境中,你才會很容易被金智婉這個形象所代表的那份孱弱和執念所打動。
當她站在破舊的電影院里,對著天光檢查膠片。
你會知道笨鳥的熱愛也是有用的。
因為她會在電影的世界里繼續堅守。
而這個“她”里面,一定也包含了“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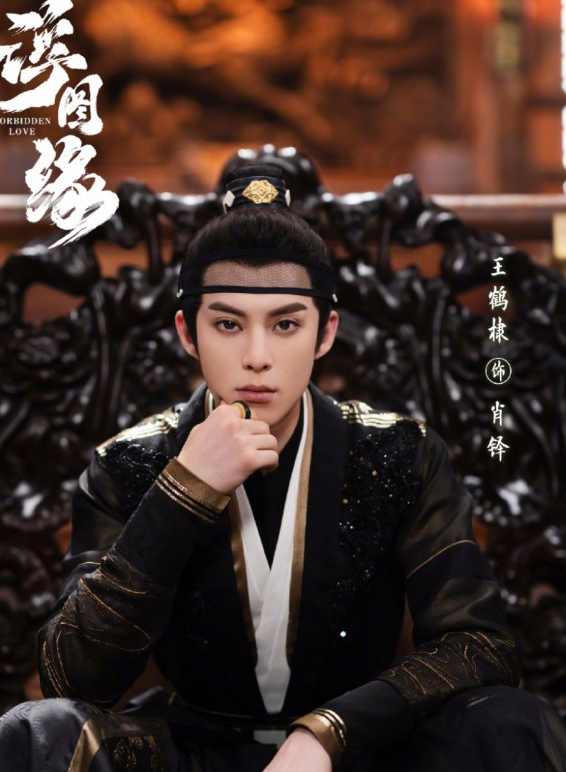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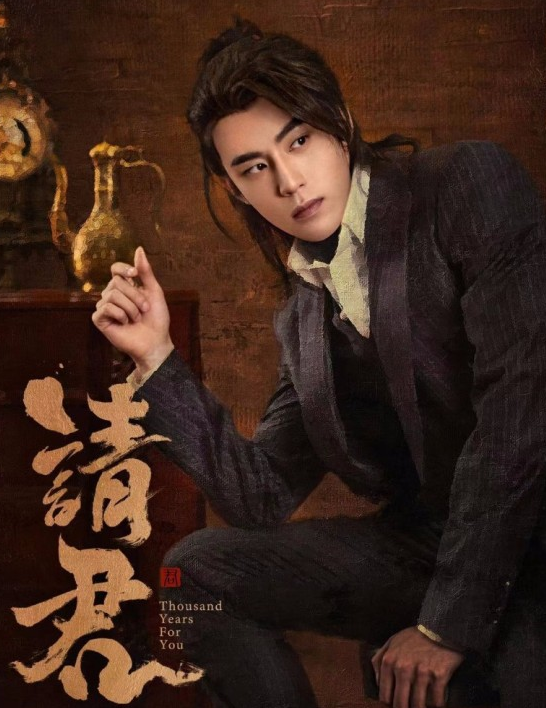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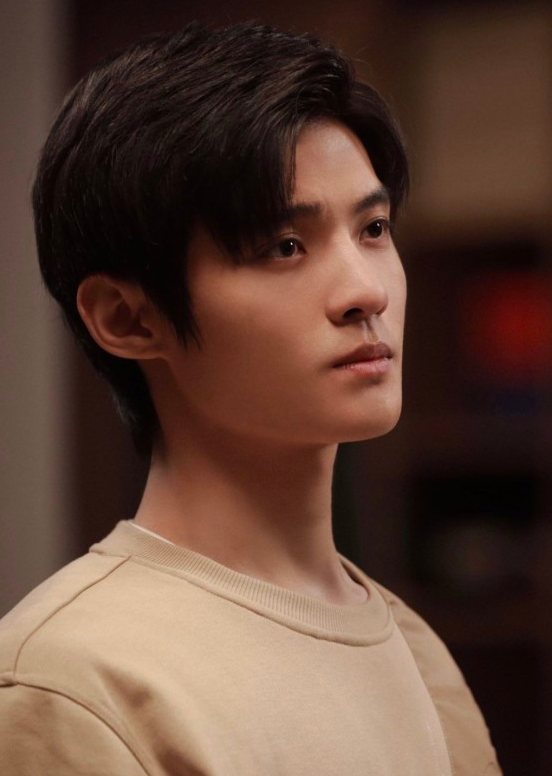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