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她》是一部非常糟糕的電影。用豆瓣一位網友的話說,“大多數電影只是平庸,《消失的她》卻稱得上邪惡卑鄙。”
它的糟糕是全方位的,討巧、走捷徑也是全方位的。從敘事邏輯、視聽語言、演員表演、服化道、音樂到電影背后的價值觀,無不透露主創者沾沾自喜的油膩品位。看這部片,就像吃一鍋狂加味精的雜肉亂燉,只記得不停加料刺激人的味蕾,吃了什么都感覺不到,最后鍋上漂著一層厚厚的油,留下那“風格”極強、味道極重的畫面,看完我對身邊人只有一句勸告:千萬不要帶孩子去電影院,時間寶貴的話,自己也不必去了。
當然還有很多觀眾感到好看。懸疑題材,國民受歡迎度高的明星主演,不停反轉,加上擦邊的女性議題,《消失的她》票房叫座,口碑也極度分裂——恰恰說明主創者對一大部分受眾喜好的了解迎合,有他們買單托底,大賣不成問題。只是我對制造“國產懸疑片天花板”的標準感到疑惑:如果這樣審美糟糕、技術粗糙的電影可稱“天花板”,今后我們還能看到什么好電影?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縫合怪”自作聰明的拙劣拼貼
《消失的她》官宣稱改編自蘇聯電影《為單身漢設下的陷阱》,已買下版權。這部蘇聯電影之前還有1986年美國版《失蹤之謎》。改編的事實毋庸置疑,但讓有閱片基礎的觀眾感到不滿的是,《消失的她》不僅改編了一部電影,還改編了很多部電影。
《消失的她》
《失蹤的謎》
它的結構既像《失蹤的謎》,又像《看不見的客人》,男主角的處境像《楚門的世界》,電影名字又像《消失的愛人》……還有許多熟悉之處,像《火柴人》、《禁閉島》、《行騙天下》等等。凡是有一定閱片量的觀眾都能明顯感到,這部電影不像一個有獨立意識的故事,反而借鑒(挪用)了太多橋段,拼湊出一個四不像的東西。它只有一點是統一的,背后是陳思誠的審美。
東拼西湊之下,故事的主要邏輯和推理也變得十分牽強。比如在上世紀互聯網信息技術尚未被普遍應用時,一個男人去警局報案稱他的妻子失蹤了,有一個冒充的妻子出現,這個故事還能夠成立。但在今時今日無處不在的網絡人臉識別系統下,一個男人身邊出現了冒充身份的妻子,卻無法判定她的真偽,實在牽強。——尤其妻子的背景還是富家千金,丈夫的潛水同事早在報紙上就能認出她,明明帶假妻子去海關驗護照就能解決的事情,千方百計繞成一團亂麻。
在《消失的她》結尾處,當倪妮撕開紋身揭露她的真實身份是受害者閨蜜時,很難不讓人想到前幾年的西班牙懸疑片《看不見的客人》。也是一位女律師,一步一步引導報案的丈夫說出案件真相和兇殺案地點,最后律師揭下面具的時刻,實現心理上的復仇,把故事推向高潮。
《看不見的客人》
《看不見的客人》自始至終都在封閉空間里,用律師和代理人的對白呈現案件的幾種可能性。精心布置的細節一環扣一環,電影敘事精簡,卻包含大量推理信息。但這樣的設定放在《消失的她》中,假律師倪妮帶著假報案的朱一龍在東南亞街頭狂飆,各種推理信息像一團煙霧彈。每每應該梳理清楚時,演員就會用一通狂躁神經發作把抽絲剝繭的邏輯游戲攪成渾水,靠制造驚悚氛圍模糊了事。不斷游戲之間,殺人的嚴肅和復仇的正義感也被削減,致使最后揭露律師身份時,有種兇手和復仇者一起玩劇本殺的荒謬感。它的整體立意就變得俗不可耐,高潮也變得可笑。
眼花繚亂難掩視聽語言的俗爛
顯然《消失的她》主創深知時下流行的短視頻技巧,只要不停設置反轉,就能最大限度刺激觀眾,讓他們大呼精彩。快節奏轉折給觀眾埋下推敲細節的障礙,往往大家還沒來得及想突然出現的情節合不合理,立馬進入下一個反轉,迅速忘記前面的漏洞。
幾番操作之下,無人在意片中人物行為的合理性,倒是能記得朱一龍坐在酒店紅和黑主色調的帷幕里,看到一個穿紅裙的“蛇蝎美人”出現,受驚不已。他的一系列驚恐、狂躁、錯亂,成功地擾亂了真正看懸疑片的智力樂趣。鏡頭反復推拉,忽而懟著朱一龍抽搐的臉頰,忽而聚焦倪妮的街頭摩托炫技——他們的良好形象成功轉移了人們對懸疑片應有的要求,只要記住朱一龍很帥、倪妮和文詠珊很美,感官上的直接刺激達到了,智力上合不合理、有沒有漏洞毫不重要。
這其中最讓我憤怒的,是主創者對自己審美的自信,已經滿溢出銀幕。不僅拍攝畫面、色調有濃濃的土味影樓風,音樂也用得極滿極俗,沒有一絲留白的空間。每當一個反轉發生時,轟隆隆的音樂就會出現,為了營造驚悚氛圍不斷濫用音效,使得聲音與沒有層次感的畫面一起制造了粘膩、聒噪不斷的不適感。
電影里還莫名設置了一些追求奇觀的情節,比如倪妮和朱一龍講到畸形秀的一段,除了制造視覺奇效讓人大呼惡心可怕,沒有別的用處。它的背后只有主創者操縱觀眾心理的得意,用畸形審美來凸顯他對懸疑片的糟糕理解。
在這樣的創作執導氛圍下,本來好好的演員朱一龍,可以用很多精巧細節去鋪墊主角人格分裂的戲碼,卻不斷秀出過時的馬景濤咆哮般的drama演技。他浮夸的肢體語言和電影濫用的音樂一樣繁冗吵鬧,不斷重復之后讓人感到深深的審美疲勞。最后即使在密閉空間里上演被剃頭的酷刑戲碼,效果也不過像前面的表演再加多味精和辣椒,嗆人,但沒有味道。
蹭女性主義熱點也改不了男性凝視的視角
在電影最后20分鐘,最大的反轉出現了。這是一個“girl helps girl”的復仇片,聰明酷颯的倪妮為了找出摯交失蹤被殺的下落,設置了局中局、戲中戲,讓男主角朱一龍困陷其中,最終交代事情的真相落入法網。
看起來是女性復仇的爽片——天臺上女孩自殺的戲碼也像極了前陣子熱播的韓劇《黑暗榮耀》——整個故事因為套上了女性主義的外衣似乎有了更高立意,但是細細看下去,主創者的男性視角始終還是主導方向。
最讓人反胃的一點就是在倪妮亮出B超照片時,一直得意的殺人兇手忽然心生悔意。他前一秒還邪魅狂狷,發現自己的親生骨肉無辜慘死就突然有了慈悲之心……那么用極端殘忍的手法謀害無辜妻子的橋段算什么呢?女人的命就不是命,孩子的命才是命嗎?
許多老電視劇都有這樣濫情的戲碼,“保女人還是保孩子”,沒想到《消失的她》至今還在用這套陳腐的敘事語言,并且依然給出陳腐的答案——胎兒生命比孕育胎兒的人的生命更重要。這個隱藏回答用朱一龍的反轉眼神表達出來,立馬推翻了前面女性力量不容忽視的虛偽假象。
還有一組男主殺人的戲碼,被浪漫美化成與妻子的凄美訣別,更讓人感到不適。被囚禁的女性尸體孤獨地漂浮在海中,創作者極盡所能表達那種唯美,令我毛骨悚然。不僅將特寫鏡頭長久地對著被害妻子的臉,還給到殺人兇手正面的鏡頭,表達他離去時的不舍和無奈。
這組畫面和前面畸形秀一樣,為了制造視覺奇觀,也帶來價值觀的困擾:引君入甕的驚悚被拍得如此美麗動人,就像一個殺人兇手炫耀自己的漂亮成績,還要表現出道德上居高臨下的感覺。它釋放的信息是:兇手不僅把人殺得很漂亮,還有他不得已的地方。這組無底線戲碼和影片最后的彩蛋連成一體,表明創作者始終站在兇手這邊,美化他殘害生命的現實,給違背良知之事蒙上了自以為浪漫的油膩濾鏡。
在創作者扭曲的生死認知面前,電影中刻板的女性形象都可以看作觀念使然。兩個主要女性人物,不是“傻白甜”就是“蛇蝎美人”,恰恰應了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厭女》一書中的犀利觀點:男性眼中女人只分兩種,忠貞的妻子和性感的蕩婦,并且兩種都是他想要的。
《消失的她》打著為女性的名義,實際還是物化女性、漠視女性生命價值。轟轟烈烈的一出假戲演完,就像臨時搭建的影棚一樣戲謔。為了填充懸疑片的各種反轉、制造驚喜,主創最終把女性生命當成一個懸置的漂亮牢籠,無人在意妻子死得多么悲哀,只會記住兇手的精神錯亂以及從“劇本殺”中走出來時,所有人都完成游戲的輕松。
這個結局對我而言是邪惡卑鄙的,我不覺得它完成了正義的聲張,恰恰相反,它削弱了死亡的沉重。大量美麗鏡頭用來渲染倪妮假扮律師的聰明,死去的妻子最后也不過像個道具,替兩位主演完成了一場心理博弈。這最終讓我感到憤怒。
在《消失的她》熱映之后,我誠懇地希望更多觀眾去觀看那些好的懸疑片。卓別林的《凡爾杜先生》,希區柯克的《電話謀殺案》,他們都關注到殺妻案背后的社會現實。人性的惡和對惡的控訴始終都是應該關注的主題,這些電影保持克制有力的敘事,讓人不忘生死的分量。
未來國產懸疑片如果以《消失的她》為制作標準,我們將會看到越來越多粗制濫造的電影。庸俗的視聽語言堆砌成反轉的狂歡游戲,最終的受益者是誰?肯定不是觀眾。
關鍵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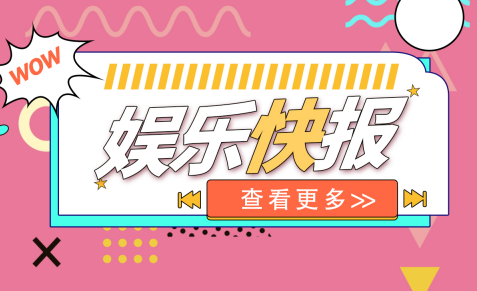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