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檔上映了八部新片,整體質量是近十年來最高的,但大盤卻遇冷
去年票房從初一到初三分別為16.92億、13.79億、14.72億;
今年票房從初一到初三分別為14.52億、10.48億和9.8億;
在這種斷崖式下跌,的背后是公眾的“三大怨”
因為疫情反復,很多地區的電影院都關門了;
第二,電影票價格飆升。9.9元看一場電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大年初一預售均價已達57.8元,比過去幾年貴了50%。一家人看電影都要猶豫。
第三個抱怨是編排混亂,一些優秀的影片得不到好的編排,其中張藝謀《狙擊手》是最大的受害者。
103010 豆瓣7.7分,是春節檔口碑最好的一個。然而卻遭遇了“陰間拍片”。
皮大年初一買了一張《狙擊手》的票,等了兩個小時,被影院告知《狙擊手》的演出因設備原因臨時取消。然后我查了一下,驚訝的發現我所在的城市要么沒有《狙擊手》預定,要么時間定在晚上23點以后甚至凌晨。
另一方面,網上對《狙擊手》《陰間排片》的抱怨太多,忙著冬奧會開幕式的張藝謀,不得不放低姿態,要求院線多排幾部。
《陰間拍片》讓《狙擊手》上座率墊底,隨后院線繼續根據上座率減少拍片數量。這種惡性循環一直持續到第三天。即使《狙擊手》的網上口碑爆棚,即使無數人為其喊冤,依然無法扭轉頹勢。
張藝謀曾經是票房保證。2000年他的《狙擊手》賣了2.5億,占當年全年票房的四分之一。現在沒有人能打破這個記錄。
現在,20年過去了,但張藝謀正在死去?
皮哥看完片子找到了答案。
一、張藝謀這部狙擊電影,“狙擊”的是國產電影的頑疾
簡單來說,《英雄》是張藝謀,對國產電影弊病的一次大膽嘗試。
這一切都始于20年前。
2000年,張藝謀拍攝了《狙擊手》,開啟了國產大片的時代。
之后的國產大片幾乎都遵循《英雄》的套路:堆明星,搞營銷,人海戰術,虛假故事,票房有多高,口碑就有多差。
這種情況在《英雄》年達到了極致,以至于連賈樟柯都感嘆,崇尚黃金的年代誰還需要好人!
張藝謀意識到了這一點,然后他拍攝了《滿城盡帶黃金甲》 《千里走單騎》 《山楂樹之戀》 《金陵十三釵》等。并盡力拍照,用小人物的故事反映大時代。
然而,其他國產電影也感染了這種“大片病”,這些年的主旋律電影都是“高大尚”和“廣鄭偉”。
這樣的片子很容易收割票房,高票房使得這種趨勢積重難返,等待它們的一定是萬丈深淵。張藝謀當初打開了那個潘多拉盒子,現在他要自己親自關上。
于是這些年他接連拍攝了《一秒鐘》《堅如磐石》《懸崖之上》這樣的“類型小片”,當然也包括這次的《狙擊手》。
《狙擊手》是張藝謀從影40年來拍攝的第一部純粹意義上的戰爭片,如果是20年前的他來拍,一定會搞大場面和堆明星。
可這次他卻反其道而行之,在宏大的命題里擷取了最微小的故事,用以小見大的方式來展現抗美援朝的偉大。
二、張藝謀拍《狙擊手》,用了4招,治好了國產電影的“病”
抗美援朝中涌現的英雄事跡那么多,《狙擊手》拍攝的背景是知名度很低的“冷槍冷炮”運動,這個運動位于整個戰爭的后期,特點就是高密度低強度,缺少名場面,可這和電影的特點卻相契合。
《狙擊手》講述的就是發生在一個不知名的小山坡上的一場局部戰斗:一個場景、兩波人,一個朝鮮小孩,幾把槍來回對射。
這種極簡主義下,反而更能激發出電影的藝術創作和情感的真實表達,張藝謀和女兒首次合作玩出了花兒。
縱觀整部電影,張藝謀總共運用了4大妙招。
第一招,借鑒SKETCH結構。
所謂SKETCH,就是素描喜劇。
相比傳統小品,它的故事背景和人物更加簡單,迅速進入劇情,針對一個笑點反復強化疊加,以產生強烈的笑果。
去年的《一年一度喜劇大賽》讓SKETCH發揚光大,張藝謀就是這個節目的粉絲,他說自己在節目還沒大火時就關注這個節目了。
印象中張藝謀不是個喜劇愛好者,他關注這個節目很大可能就是SKETCH這種形式吸引了他。
在《狙擊手》中,張藝謀不僅是導演也是編劇,他就采用了這種SKETCH的創作方式。
單一的場景,簡單鋪墊后迅速進入雙方對射的回合制游戲,然后針對對射這一個點不斷強化,制造出一番、兩番、三番甚至是四番的效果。
同樣是對射,我們看到了戰術的迭代與升級,從假裝挖戰壕,到雪地里翻滾對射,再到交換班長,以及最后的用勺子勾火,聲東擊西完成致命一擊。
SKETCH的應用使得重復的敘事不再讓觀眾厭倦,反而大大增加了觀眾的期待感。
第二招,麥格芬手法。
SKETCH畢竟只適合短劇,無法撐起一部電影的長度,于是張藝謀又采用了麥格芬手法。
麥格芬手法是希區柯克發明的方法,簡單來說就是代表“懸念”的人和物體,它在全片中可能都沒怎么出現過,但就是牽動著觀眾走到最后。
《狙擊手》中的麥格芬就是那個傳遞情報的亮亮。
他在全片中幾乎都是躺著的,戲份不多,但因為身上有情報,一下子把觀眾的注意力吸引過去了。
他的每一個動作和表情都拉扯著劇情:
無論是身上藏著情報的傷口,還是用針管給自己注入空氣,亦或是那份血書,都讓平淡的劇情一下子變得陡峭,滋生出茂密與繁盛,最終他在狹窄的空間里完成了情報的傳遞。
片尾謎底揭開時,觀眾竟然有了一種看諜戰片的快感。
第三招,巧借“一頭牛”。
在數學里有個經典的“分牛困境”:
農民把17頭牛分給3個兒子,大兒子得一半,二兒子得三分之一,三兒子得九分之一,不能殺牛,只能整頭分。
乍一看,這個題目無解,可是只要“借1只牛”,就很容易算出大兒子分9只牛,二兒子分6只牛,三兒子分2頭牛。
三人分完17只牛,那頭借來的牛也可以物歸原主。
在拍攝抗美援朝題材電影時也會面臨“分牛困境”——
這場戰爭參與者有中、美、朝鮮、韓等多國,如果全都交代,容易造成混亂,所以過去的抗美援朝電影都會自動忽略朝鮮人,將戰爭簡化成中美直接的強強對話。
可是《狙擊手》卻巧妙地借了一頭牛,這頭牛就是影片中那個朝鮮小孩兒。
觀看影片我們就會發現,中美雙方劍拔弩張,朝鮮小孩兒卻自由地穿梭于戰場中,明明憨憨傻傻,卻愣是活到了最后,而且還毫發無傷,這不就是那頭借了又物歸原主的牛嗎?
可是因為他的存在,一攤死水的局面被攪活了,他像一個催化劑一樣,讓雙方的較量不是隔岸觀火而是聲臨其境,而他本身具有符號意義,代表了當時復雜的國際形勢。
這頭牛,借的真妙!
第四招,削去棱角。
張藝謀這片兒就是要歌頌不被歷史銘記的平凡英雄,為了強化這個主題,他甚至“自廢武功”,削去了影片所有的棱角,讓我們再也看不到那個熟悉的張藝謀。
片名上,他直接把《最冷的槍》改成最為通俗的《狙擊手》;
演員上,除了章宇和張譯,他使用的幾乎都是“素人”式演員;
場景上,他將所有的故事盡量濃縮到單一的場景里;
畫風上,也拋棄了自己擅長的色彩美感,追求極度寫實,士兵中彈的場景讓許多人看著揪心。
敘事上,他也故意做了“退化”,大量引用了主角的旁白,這在電影拍攝中本該是大忌。
甚至在電影宣傳上,本片都低調至極,在春節檔上映前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有這部電影的存在。
張藝謀像個笨拙的新人一般,拍了一部沒有特色的電影,然而沒有特色恰恰就是本片最大的特色,因為它謳歌的就是那群“沒有特色”的人,就像影片旁白說的那樣:“我的戰友都犧牲在那個無名的山坡上,只留下了一個個普通的名字。”
影片結尾,五班在激戰后只剩大永一人,他痛哭流涕,這時候張譯飾演的連長告訴他,五班還在,希望還在。
他開始點名:“劉心武、米老二、胖墩、孫喜,小徐…”
他念出這些死去的戰士的名字,很快新的戰士紛紛回應道:“到!”“到!”“到!”
這是影片最大的淚點,也告訴我們,真正的狙擊手不只是報紙上記載的個別的名字,我們的志愿軍里人人都是英勇的狙擊手,即使歷史已經把他們遺忘,但是有人會記得他們曾經來過。
當然張藝謀也為自己的勇氣付出了代價,《狙擊手》因為芝麻上雕花而很難被看見,因瘋狂做減法而在春節檔遇冷。
但反過來,它也像一顆冰冷的子彈一般,給票價浮夸、宣傳浮夸、電影品質浮夸的春節檔來了一次狙擊。
這不是螳臂當車,而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隨著春節檔大盤遇冷,隨著張藝謀的主動求變,我們應該能纏繞在中國電影身上多年的“大片病”應該會有所緩解了。
不過,酒香不怕巷子深,在如今口碑為王的當下,我們相信,《狙擊手》定會在春節假期后,完成翻拍逆襲,借用觀眾的一句話:張藝謀,別著急,我們還有時間!
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文/皮皮電影編輯部:一粒雞
?原創丨文章著作權:皮皮電影(ppdianying)
未經授權請勿進行任何形式的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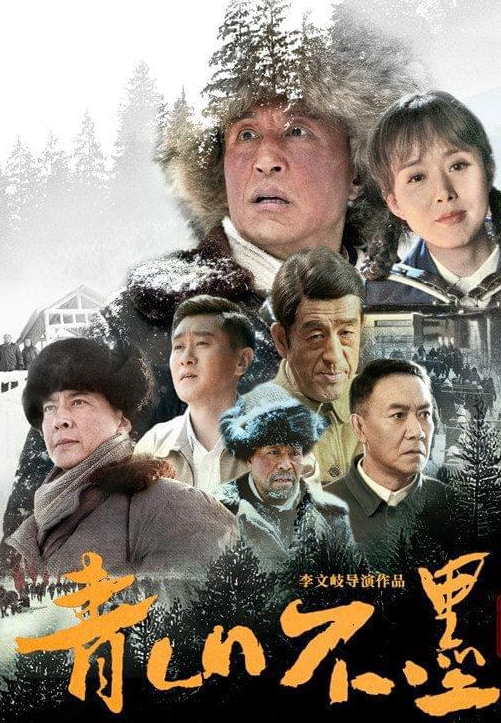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